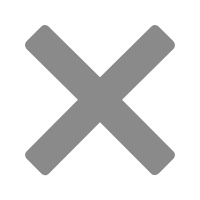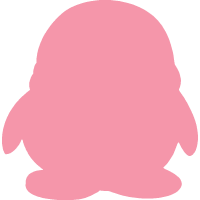第 11 章节
地的一片银装。地上堆积的厚厚白雪,也显得格外亮堂。这个夜,倒是活络了起来。红鸢依旧一身亮眼的红裳,火红的狐裘,衬得她精致的小脸说不上的贵气。
扶着红鸢进房,侍剑匆匆带上了房门,阻隔了门外冬夜的严寒。
屋内早就生了炉火,极暖。红鸢怡然地解下裘衣,递给了侍剑,水衣在这时转过了脸来。似笑非笑地盯着红鸢,不开口,也不靠近。因是夜,风极重,白日里打开的纱窗此时已经合上,只是水衣,习惯地站在纱窗旁。
嘴角含着笑,浅浅地望着红鸢。
刹那间,红鸢突然明白,原来这世间还有一种笑比哭更动容。挑了那张自己最常坐的木椅坐了下去,红鸢别开脸避过水衣投来的清澈目光,声音低沉地几乎听不出往日里的意气风发,她说,
“小衣儿,我真的没有想到你竟是煌宫的凤尾,还有月终天和离楚歌。”当年的那件事情,虽说是祭月之城和煌宫私下的事,但四大世家也是收到风声的。不过,知道的也不多,就知道是煌宫的凤尾宫主爱上了别人,硬退了月终天的婚。
红鸢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凤尾爱上的人居然是南源香雪海的离楚歌,也难怪当年这件事被瞒得滴水不漏,离楚歌和鹫谷的云朵瑶,是早有婚约的。凤尾和离楚歌那一闹,折得不仅仅是祭月之城和煌宫的面子,还有香雪海与鹫谷,不谨慎些怕是会烽火再起。
只不过,这兜兜转转的,现如今的结局还是回到了起初的原点。
离楚歌与云朵瑶,就要成亲了。
“小衣儿!”红鸢终是抬起了头,声音又是低了低。
“离楚歌要立后了!”理智告诉红鸢,这件事不应该告诉水衣,但直觉又是驱使着她将这事儿给说出了口。
他要成亲了。水衣的笑靥刹那间凝固在屋内明媚的烛光,如同秋华挽月的眉梢看不出情绪,也读不到忧伤。星辉眸底跃跃的几抹光华,缓缓流淌,翛然无声地撞击着人的心房,斑驳了天际最为绚丽的霞彩。
与他相处了三年,他从来都没有说过要娶她,他说,我们会在一起的于这梵山之上,一生一世。水衣从来都不知道,原来这算不得誓言。
有些紧促地理了理飘远了的思绪,水衣晃过了神来。再次望向了红鸢,道了声,
“哦。”声音已是平淡得不见一丝波纹。
红鸢竟是有些着急了,再开口,
“婚期就定在了来年的开春!”
“你想让我去?”水衣微微挑了挑眉。
红鸢顿时不再言语,于是水衣继续接下道,
“那,便去吧!”
“其实!”红鸢又是抬头,
“若是你当真不愿意,可以不去的!”
于是,水衣又笑了,轻声道,
“你不是想让我将那伤口内的脓挤得干净么,此番不去,如何能让过去死得干净?”
接着,红鸢也笑了。水衣聪慧的心思,连她自己也是自叹不如的。只是,情关难过,连水衣如此慧质的女子,也参不破一个“情”字。那她自己呢?没有来由的,红鸢心里浮现了那张冷峻的面容,心,猛地抽痛。神色,也黯淡了下来。
“那你呢?”不知何时,水衣已经坐到红鸢的身旁。
“什么?”红鸢佯装不解,偏着脑袋望向了水衣。她就知道,凡事都瞒不过水衣。
水衣倒也不点破她,继而风平浪静地道,
“这些日子,在幕水之滨还好吧?”
红鸢忽得脸色一变,差点没从椅子上摔了下来。淡定着声色,镇定地道,
“还好!”后似是想起了什么,猛地站立起身,连连告辞水衣,
“小衣儿,本主想起今晚还有事需处理,先走了。”匆忙的脚步,让水衣不由得想起了一个词,落荒而逃。很突然地,水衣就笑出了声来,对着红鸢的背影,淡淡地道,
“若能深爱,切莫放手!”
果然,引得红鸢的脚步一顿,最终,还是踏出了房门。
十.
十里樱花渡,一夕香满朝。
阳春三月,真是春暖花开的好时节,樱花渡里的十里樱林,粉紫枝头,花瓣编织的霞彩艳丽了渡口的颜色。
水衣静静地站立在甲板上,目光追逐着两岸的樱花,眸底蒸腾起了一片寂静的黯然。藏得太深,所以没有人能看透,那寂寞就像是阳光下的一点阴影,如此微薄,却又如此无可避免。
这香雪海的樱花渡,就像是一场梦,一段情,一系结。牵扯了过去,但又无法展开未来。只是无边无际的失落,绝望。
曾经,水衣听得有人说过,身上的伤口是极易医治,但心里的伤口却得用时间去熬一贴良药。也许,就是一生。
可是水衣是真的不知道,要忘掉那段过往,得多久?一月,一年,十年,还是一生?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过了樱花渡,下了船,就算真正踏入了香雪海的内城。前来迎接的轿子,早已侯在那儿,只等着红鸢和水衣上轿。
此番前来,水衣等人是算好了时间的,拿捏得很准,正好赶上了封后大典。水衣和红鸢作为秋水霜的使节,与月终天等人一齐被邀请于沁雪台,参与祭天。
此时,离楚歌挽着云朵瑶站立于高高的祭台之上,十指交缠,四目相对,眸光流淌的情意淅沥缠绵,说不出的潋滟和旖旎。身着堇色巫袍的祭司们站立了两行,守于祭台的两侧,也只有大祭司站在离楚歌和云朵瑶身旁,双手恭敬地捧着祭文,虔诚地大声拜读着。
到底大祭司在读些什么,水衣是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她只是看到了离楚歌一身吉服,如沐春风,气宇轩昂,英俊的眉眼微微低垂,隐隐可见款款浅笑,依稀表露出心内的喜悦以及欢愉。温文尔雅之下轻荡的流光,如同晨曦破晓的第一道曙光,明亮地让水衣移不开痴迷的眼眸。
往事恍如淙淙流水,潺潺于脑海中流淌。
最远,也不过十年之前。她在凌海学琴,碰巧救了一个被打得认不出面容的少年,虽然明知道那少年是个不入流的偷儿。因为,在对上那少年眸底的坚毅和毫不隐瞒的磊落时,她的心,不知怎的就软了下来。
和离楚歌对上,确是无意。他似是和那少年有仇,卯足了劲儿和那少年对上。她自是要护着那少年的,不得已抬出煌宫小宫主的身份来压他,这才知晓他竟是香雪海的少君。而原来,居然是那少年偷了他的信物,才逼得他跟那少年对上。
她既是掺合入了两人之间,那事她是不能袖手旁观的。经她调解,那少年总算将他的信物还了他,他也答应放那少年一马。虽说和解,可他与那少年的积怨毕竟已深,相看两不对,言语之下都能动起手来。她拦都拦不及,许是那少年被他打得怕了,某天醒来,不告而别。
他,依旧留了下来。合着怎么都是她的不对,欠着他一个人情,不好赶他,也就让他留了下来。
她在凌海学琴一年,他就陪了她一年,在这些个日日夜夜地相伴中,不知不觉,情根深种。在她离开凌海返回煌宫时,他拉住了她的手,很是不舍地问,我们,还能相见么?她笑了笑,答,若是有缘。
本来,她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