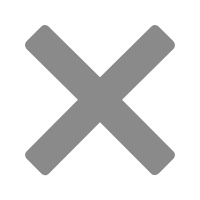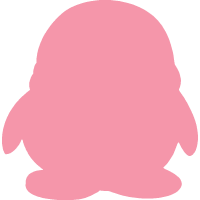第71章 鬼推背
上午十点半的样子,我开车到了村长家的门口,大门只开着一道缝隙,里面脚步声声,我只听到村长的小儿子接电话的声音。
在电话这边,他表现出一副很听话的样子,连连打着保证:“好,好,你放心,这我是清楚的,我一定约束我们家人不出门,尽量配合好公安的工作……好,我听你的,我知道……”
怎么,他们家居然都不让人跟着我去把遗体送到殡仪馆?
提起这个,我其实特别疑惑,村里都是土葬,很少见火葬,怎么这一次发布的任务居然是把村长的老婆带去城里火化了?
并且,疑惑远不止这一点,村长也死了,为什么没说要把村长的尸体也带走火化?
我本能地觉着,这事情有蹊跷,可蹊跷在哪里,又说不上来。
他们总不能借着这个由头把我杀死吧?
我赶紧给胡大叔打了个电话,让院子里的人都听到的电话。
对话中,我很大声地直说了我的担忧,但胡大叔表示我是杞人忧天。
他说:“你尽管放心大胆地干你的工作,你所担忧的那些问题,说个不好听的话,那正是我所希望发生的事情。你不要忘了,我大老远从京城下来是干什么来的!”
疯子和夏小洋,甚至小刀和斧头都宽慰我不用这么杯弓蛇影,我这才安心。
可我心里,到底还是那个疑问挥之不去的,为什么村长老婆要拉到城里去火化?
家里死了两个老人,村长的小儿子很忙,带着冷漠的敌意,他甚至没有特意来和我多说一句话。按照收费付费之后,他老婆只交代我明天他们会来领取骨灰盒,就把我送到了门外。
村长的老婆,死相很惨,也没有棺材之类的,就给她穿了寿衣,用宽布条固定在了出租车的副驾驶上,这还是我要求的。
我可不想认真开着车呢,后面冷不丁发生点什么事情。
还好,路上没有发生任何状况,一直到了火葬场里面的殡仪馆里。
殡仪馆和火葬场是一个单位,前者在前面,后者在后院,我先感受到的,是整个殡仪馆。整个空旷而森冷的殡仪馆里,我只见到一个一个眼圈很黑,沉默寡言的中年妇女,经过自我介绍,我知道她姓张,我称呼她张姨。
而且,这个张姨,当我问起那个中年人的时候,她竟告诉我她是他的婶子。
那火葬场的中年人这两天都没过来,说是家里有点事情,请假了。
家里有事?
我心里冷笑,恐怕是亲戚家里吧?大概这会儿,他已经和村长的小儿子联系好了。
在殡仪馆的门口,张姨从我车里接过了村长老婆,无意中,正在观察她的我没注意碰到了她的两根手指——好冷啊,跟冰棍恐怕也没多少区别了吧?
最让我对张姨印象深刻的,不仅仅是她烟熏妆一样的黑眼圈,还有那张惨白惨白的脸,若非脸膛上还带着些微的活人才有的红润,我恐怕不敢和她在一起呆一秒钟。
她个头不高,但也不矮,不到一米七,却佝偻了腰,总是哮喘一样的喘着气,时不时沙哑的咳嗽一声,黯淡的肤色下,早已走样了的身材总是摇摆着,可看她毫不忌讳地抱起村长老婆的尸体一点不费劲的样子,我判断她的体力很好。
想想也是,在殡仪馆上班,总要搬运死者的尸体,据说死了的人特别沉,要没点体力,那怎么成。
带着我进了大开着门却越发冷清的殡仪馆,泛着沉沉死气的味道立刻扑鼻而来,我差点没呕吐出来。
张姨回头看了我一眼,她冰冷的目光中,好歹还有点温度,安慰我说:“你一定要适应一下,既然死者家属完全嘱托你负责死者遗容的整理和火化,你就得在这里待小半天,小心别冲撞了什么,那就不好了。”
我唯有忍着胸口沉甸甸的想吐的欲望点点头,乖乖听话:“好的,张姨,我会很快适应的。”
张姨满意地转过头去,带着我继续往松柏掩映里的二层却很长的小楼走,一边传授着她的心得体会:“其实,你也不用着怕,人么,无非就两种,死了的,活着的,没啥区别。”
死人和活人,那能一样么?我对这地方,越发地抗拒起来。
张姨显然能感受到我心里的抗拒,只是咧着嘴无声的笑了一下,把我吓了一跳——不是我犯贱,别人对我笑我还矫情地不乐意看,而是那张在室内就显得更加惨白,而且还带着灰扑扑的死气的脸,这一笑配上她那副焦黄甚至焦黑的牙,实在让人渗得慌。
“走吧。”来到小楼的一个比较狭窄的单间里,她把尸体靠在脚边,自顾自地套了一件白色的类似医生那样的大褂,指了指挂在墙脚一架上的另一件崭新的白大褂,没让我穿,但我明白她的意思。
于是手忙脚乱赶紧穿上大褂,我怀着极度的忐忑,亦步亦趋地跟在又扛起尸体的张姨身后,出了休息室,在长长的静谧而森冷的泛着幽幽蓝光的走廊里,听着两个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迟钝,越来越迟钝,终于心里生出一个恐怖的想法:“在这鬼地方,是个人都得疯吧?如果没疯,是不是就半人半鬼了?还有,如果一个鬼看着自己的身体被火化,难道就不会发疯,突然袭击人?”
我渐渐感觉到了身体内部血管里雪夜都在慢慢冰凉,呼吸渐渐紧促起来。
偶然经过一个半掩着门的屋子,里面柔和却依然冰冷的蓝色灯光下,我看到一张微笑着的脸,除了眼睛是闭着,那人就跟大活人一样在看着我,正对着我的眼睛,他在冲着我笑。
我一把捂住自己的嘴,把那一声惊恐的尖叫憋回了肚子里去。
张姨突然嘿嘿的笑了起来,我汗毛倒竖,如闻夜枭啼哭般反应。
“那是整理好的一具尸体,正常死亡的,没啥大惊小怪的。”笑完足足等了有半分钟,张姨停下脚步半侧着身体,才淡淡地说道。
我哦的一声,四下里张望着,怎么不走了?
“到了。”张姨推开她正对着的那间屋子的门,里面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清。
我不敢随便走进去,听人说过,这家殡仪馆的屋子都很小,空间不是很足,千万不要在里面随意的走动,说不准一不小心就碰上存放的遗体。
啪的一声,张姨打开了灯,把肩头的尸体放在了一张匣子一样的床上,而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具距离我不过两步之远,平静地躺在一张木板床上的尸体。
那是一个很年轻的死者,清清瘦瘦的样子,生前一定是个很标致的年轻人。
可我往他脸上一看,顿时头皮炸裂了一般。
只见他一双眼睛大幅度地瞪着,铃铛似的,眼角已经破裂了,丝丝已经凝固的血,在耳根处汇聚成一块血块。他的脸,扭曲的厉害,五官纠结的彷佛一团乱糟糟的麻绳。
他的躯体,虽然被洁白的被单盖着,可与他的脸庞一样扭曲的形状,我还是看的清清楚楚。
“他,他是怎么死的?”我猛的吞了一口口水,忍着打寒颤的冲动,用手碰了碰张姨。
张姨从我旁边往门外走去,随口道:“不知道,反正是惨死,整理起来很麻烦。所以,你很幸运,没摊上送这么个尸体来。”
听她说的极其随意,就好像面前的尸体真是一盘麻绳,我想,她一定是见的多了,所以才会这么麻木。就跟法医一样,各种各样的尸体亲手解剖的太多了,早已不惧这些臭皮囊了。
可我恐惧啊,恐惧的厉害!
村长老婆是喝了毒药又上吊死了的,整个人已经青紫了,居然还要出现这么一个恐怕身体都已经支离破碎了的尸体,我又想起那个杀我未遂却把自己弄死了的重卡司机,没来由地一阵阵心慌。
“你,你干嘛去?”张姨居然出了门去,我更为惊恐,连忙窜出去拽住她的衣袖问道。
张姨挥手很轻描淡写就挣脱了我的手,从裤兜里摸出一包很便宜的红梅,以及一个一块钱的打火机:“抽烟。”
是了,工作室里是不能抽烟的!
可是,你要走了,我怎么敢一个人在这呆?
“放心,我就在门口这,不过十来步的距离。”张姨张着满是黑牙的嘴巴,皮笑肉不笑地愈发让我恐惧。
你最好还是别笑了吧,更吓人!
“今天就我一个上班的,一会儿还要送尸体到火葬场去,你得帮我先整理好这女人的脸,把舌头啥的塞进嘴里去。”张姨说。
接了任务,我无可奈何,只好听从她的吩咐,用工具撬开村长老婆的嘴巴,把舌头给她塞进去。
工具箱就在尸体头部的“床头”前面,我战战兢兢的一边给自己壮着胆,一边哆哆嗦嗦绕过尸体,来到工具箱的前面,弯下腰,伸手抓住了工具箱的提手。
就在这时,我忽然感到右肩膀上被一只手狠狠的推了一把,那力气大的出奇,我根本没法控制自己,不可避免的一头往地上扎去——如同一只巨大的青蛙,一个猛子往水里扑去一样。
哎呀——
我大叫一声,眼看就要无可避免的撞个头破血流了,却又感觉到肩膀上一双老虎钳一样的手把我牢牢地挽住了。
回头一看,死人脸一样的张姨瞪着眼睛看着我。
我以为是她在跟我开玩笑,勃然大怒,但没等我破口大骂,只见张姨对着那具恐怕用破碎来形容都不过分的尸体冷冷地道:“死都死了,还想害人吗?”
一股寒流,直从我的脚后跟扑上了后脑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