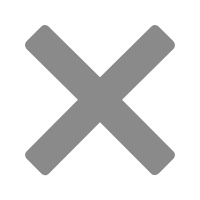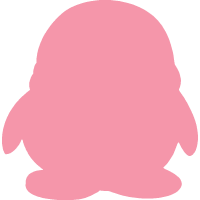第 9 章节
发,肺衰而亡。
外公外婆白发人送黑发人,拉扯着外孙,就靠着外公一点退休工资和外婆帮村里打扫卫生那点收入艰难度日。好在后来,跨世纪之初遇到拆迁,家里分到两套房,一套80平米,一套50平米。
邹辉和外公外婆挤在一套大点的公房里,一套小房就出租给外地来沪的打工者,一个月好歹也有个几百块房租贴补家用,老弱病残的一家三口总算是松了口气。
可还没等这口气松下来,老两口嫁出去多年的大女儿率领老公、儿子,还有那个已经号称“断绝父子关系”的二儿子一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浩浩荡荡,挤挤攘攘,拖儿带女,理直气壮地要求回家照顾二老。
邹辉外公是个工厂门房间保安,一辈子老实本分,知道这两家人来者不善,都是冲着这点祖业家产。气不打一处来,可又憋不出什么粗话气话狠话,只知道一个人端了阿凳(凳子),坐在小区门前河浜边上,闲看人家在放生桥上钓鱼。
外婆是个秉性善良淳朴的农村女性,加之对孩子天生舐犊情深,看着大女儿和二儿子两家人都聚得齐齐崭崭,心里像股蜜糖扭扭得来,直冒糖水,自己再苦再甜也心甘情愿。从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
早晨煨的白粥滚烫稀稠得当,配的酱乳瓜、姜丝、白水蛋、油条;中午还要伺候两个大爷吃饭,一个是大女儿,另一个则是儿媳妇。菜咸了不吃,淡了更是横挑眉毛竖挑眼。一个说自己不吃肥肉,要减肥;另一个说成天不见荤,饿都饿瘦了。
晚上就更不得了,大女儿家三口人,二儿子家三口人,加上老头老太太和邹辉,一家九口人挤在一张油漆剥落得斑驳不堪的老方桌旁。只见筷子飞舞,菜叶旋转,肉团你争我夺,就看见一个个唾沫溅出,眼珠子瞪得老大,好吃点的菜转个背就只剩下汤汤水水,不好吃的谁都不睬。
有几次邹辉放学回来晚了,就看见外公外婆枯坐在桌前。两个老人两张脸,越长越像的夫妻相:干瘪、枯槁、黄瘦,像两颗风干的枣核。再看饭桌上:八个盘子,六个已经空了,浓油赤酱的汤汁滴滴答答洒满了桌面,鱼骨头、肉骨头、菜帮,混在一起,已经分不清原来的面目。而剩下的那两个碟子里,也只是一盘炒雪菜,另一盘已经不知道是什么菜,只剩下几片黄瓜。
邹辉抬头一扫屋里厢,两间卧室房门紧闭,原来孃孃家(大姨)和舅舅家各自占了一间房,一家人在房间里头噶三胡(聊天)呢!时不时还爆发出阵阵欢笑声,尤其是舅妈的声音最刺耳,像尖利的指甲划过玻璃的刮擦声,让人耳膜生疼。
十六岁的邹辉这次再也忍不住了,怒不可遏,一把推开两扇门,两个老人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什么事,就听见邹辉高声斥责道:“外婆快七十岁了,天天洗埋汰烧,忙得脚不沾地。你们年纪轻轻,不搭把手就算了,怎么忍心这么对他们?”
“哟!”舅舅首先跳出来,“迭个家啥辰光轮到你说话了?”“就是啊!”舅妈也开口了,“姆妈开心帮阿拉烧饭,她和阿爷看到小辈们吃得香喝得香,勿要太开心(不要太开心)哦!侬个小赤佬操啥心?”
“你们成天又吃又喝,给过他们一分钱吗?”孃孃脸上也有点挂不住了,“喂,邹辉,我同侬讲,什么钱不钱的,还轮不到你指手画脚。阿拉爷娘和自家儿女不谈钱,再说,我们吃点喝点也不会亏待他们!因为伊拉(他们)还指望我们养老呢!倒是你,侬看看侬,姓不是跟我们一个姓,自家爷(自己爸爸)还是个外地人,你妈妈出嫁了还能在娘家住,吃爷娘的,喝爷娘的,临末了还要分一套房!凭啥阿拉当姐姐哥哥的还不能享受?啊?今朝侬倒是跟我讲讲清爽!”
“好了!”外公实在看不下去,气得把碗筷往桌上重重一搁,本来就摇摇欲坠的桌子板凳也跟着晃起来,一家人这才安静下来。
邹辉虽然才十六岁,却也有接近一米八的身高,可面临这个情形,只能把拳头死死捏住,额头青筋爆出,不争气的眼泪却在眼眶里打转。“都少说几句!辉啊,侬先去吃饭!”
毕竟少年气盛,邹辉一气之下推开大门,冲出去了。
外婆一看,急得血涌上头,几近晕厥。外公也煞白了脸,跟在后面追了好几个街口。
那时候四周还远没有今天的繁华,坑坑洼洼的路面,偌大的路口,只有一盏路灯,还是半明半暗,让人瘆得慌。
一条街上行人寥寥,只有外公苍老的声音在回荡:辉啊,侬快回来,唔要想不开!躲在暗处的邹辉,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住了。自己从一堆砖头木片后跑出来,一把抱住外公,嚎啕大哭。
邹辉的眼泪倒不是为了刚才孃孃舅舅说的那几句刻薄话而流,只是自己幼年丧父丧母,如今任由他人践踏,尊严全无。 十六岁的少年扑在外公怀里,抽泣着:“外公,凭啥我没有爸爸妈妈?”年迈的老人无言以对,只有爱怜地抚摸着邹辉的头发。
自此,邹辉发奋读书,考上警校,重新捡起父亲的旧行当。正准备回报外公外婆时,两位老人也因营养不良,身体虚弱,先后去世了。
这时的邹辉已是初入警校,成为一名警察。果然不出意外,两位老人一去世,他们的一对活宝儿女就为了这两套房子的归属争得面红脖子粗,大打出手,几度闹上法庭,但终因老人事先有先见之明,早早立下遗嘱,并由邹辉找到律师公证:50平米的房子作为遗产留给邹辉,80平米的那套由大女儿和儿子平分。
邹辉的孃孃和舅舅两家这才放弃对50平米房子的觊觎,转而开始对80平米房子的抢夺拉锯战。
一个说,姐姐是出嫁之女,房子应该由儿子继承,最多意思一下,给姐姐十万块补偿补偿。另一个说,爷娘遗嘱写得清清爽爽。让我们“平分”!侬想独吞,没门!两家人拉拉扯扯,持续了一两年辰光,这当中,邹辉拎了自己一个小包,就搬出来住。至于后来孃孃家儿子找了一群混混狠狠教训了一顿舅妈,让她别在中间挑拨离间。舅舅又吵上门去,打120的,报警的,简直可以写一部本地人争夺拆迁房的剧本,这都是后话了。
作为一个童年失去双亲,受尽贫穷、歧视与白眼的少年郎,邹辉以后真的秉持了父亲嫉恶如仇的侠气,骨子里又有母亲体恤弱小的善良。
他一个人默默上班,默默下班,不交际不娱乐不抽烟不喝酒,只喜欢静静看书,尤其是侦探的书籍,被别人誉为“警痴”。
邹辉前后交过两个女朋友,一个是大学同学,嫌他太直男做派,没有一点情调,不会出手阔绰给自己买礼物,请自己出去吃饭,逛街,创造惊喜,谈了两个月就分道扬镳;
第二个女朋友甚至都算不上女朋友,就是进入警队以后一位女同事的闺蜜,因为对穿制服的人有一种天生的崇拜感和新鲜感,天天缠着闺蜜给自己介绍警察。女同事盘算下来,只有邹辉还未谈婚论嫁,于是就撮合两人见过几次面。闺蜜是个心直口快,精明势利的泼辣女人,见过面之后私下一打听,邹辉家里无父无母,无产业,无多余房产,无积蓄,属于典型的全无人员。转念一想,这身制服又不能当饭吃,于是就熄了这股热情,讪讪的,留了个微信号,就再也没有下文了。
遭遇这些人世起伏,邹辉觉得人海茫茫中,再也没有什么值得自己倾心托付的人和事,唯有层出不穷变化莫测的案件让他心脉喷张,热血沸腾,所以已经三十多岁的邹辉依旧孑然一身,早出晚归,沉迷于破案之中。
经过昨天朱甘强这么一出,邹辉回到家中,往单人床上一躺,大脑仿佛被打开了一个通道,透进一线光,他开始睁开眼,昂着头,迷茫地看着周遭,万事万物混沌空濛,在无形空中漂浮旋转,让人目不暇接。邹辉看着看着,昏昏沉沉地将睡欲睡,迷迷糊糊中,他好像听到一个声音在遥远的虚空中,轻轻呼唤他。
他费力地想睁开眼,无奈实在太困,眼皮沉重,他终于放弃了,合上眼,沉沉睡去。睡梦中,他清楚地听到两个字:
“不退!”
二十三、层林霜染 总是离人泪
林秀娟立在李万翔办公桌前,也不知过了多久,才如同一只将将苏醒的冬眠昆虫,探出头来,左右环视,缓缓地拿起那张揉得皱巴巴的离婚协议,似看非看。
薄薄一张A4纸,在自己手中重达千钧,眼前一个个方块字如同铅块,攥在手中,却好比堵在心口,沉甸甸地让人喘不过气来。
再看看对面坐在沙发上看手机的李万翔,这个曾经是自己生命中最珍贵的一个天赐之物,自己所有幸福赖以生存的根源,从昨天到今天,整整二十四小时,林秀娟觉得自己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一下子攀登到喜悦的疯狂巅峰,一下子又跌到了人生中的绝情谷底。
大喜大悲,苦乐哀怨,爱憎离合,人生情爱,不过如此。想到这里,林秀娟蓦地升起一股索然离世之感,曾经的她,以为自己这前三十六年已经站到了如此高度,注定了就是人生赢家,而且会一直持续下去。
让她措手不及的是,人生如落花流水春去也,一朝逝去永不再来。自己所赖以生存和荣光的赢面,不过是只不堪一击吹弹即破的纸糊花灯。
你看它在空中飘摇旋转,光怪陆离,让你晕眩,让你沉醉,让你痴迷,让你以为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待到佳节一过,韶华逝去,花灯就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消失不见。而自己手中,空空如也,不仅如此,连后半生生存都大成问题。
如果时间可以定格,林秀娟情愿永远停滞在昨天晚上她和李万翔相拥的那一瞬间。
两个小时以前,李万翔接到林秀娟的电话,全身如同电击一般刺痛,耳旁雷鸣轰隆,握着话筒的手颤抖不已。他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地经营着自己的家庭、公司、妻子、儿子、情人、客户,千算万算,以为自己算得滴水不漏,每个人的价值都被自己充分发掘利用起来:妻子在家操持家务、照顾孩子老人亲戚朋友、迎来送往,对外维系自己的脸面;情人在外风流快活、弥补自己对逝去时光岁月的惶恐;员工在公司勤勤勉勉、任劳任怨、怀着对自己老板的崇拜近乎缥缈不可得的爱,为他付出毫无怨言;客户面前装孙子,可以拿到更多项目,结识更多人脉,赚到更多钱……
这样的人生,精刮细算,八面玲珑,四方来拜,精彩纷呈,无与伦比,李万翔真的做梦都要笑醒了。可眼下发生的一切,让他忽然意识到,原来做梦多了,会把现实和梦境混淆一体的。
情人怀孕了,儿子被绑架了,客户把自己给玩了,仇家盯牢自己,——李万翔拼命地摇着头,用手死死掐着胳膊,一阵阵疼痛穿心而过。
怎么办?李万翔忍不住用话筒敲着脑袋,完全忘了周娜正虎视眈眈地站在对面逼婚呢!
“不行,不行!”突然间,李万翔想到了什么,脱口而出,“我要报警,马上报警!”
一只纤纤玉手横空伸过来,硬生生地把李万翔正准备拨打电话的手按下去了,李万翔抬起头,看见一张秀美精致的脸庞,如水一样的眼眸静静地凝视着自己,相形之下,别人都显得那么粗笨拙劣,唯有面前这个人:古水无波,眼中含情,充满了智慧与柔情。好像上帝派来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的天使。
“你干什么?”
“万翔,这个时候,报警不能解决问题。”
“那我怎么办?坐在这里等?!等着绑匪撕票?”
“盗亦有道,对方这么做,肯定是有目的的,如果能跟对方联系上,满足对方的要求,他们一定不会为难你的。”
“可眼下,让我到哪里去找他们?找到了,万一他们狮子大张口,我怎么办?”
“我有个哥哥,在老家就是专替人打抱不平,黑白通吃,他有好多兄弟,这方面会有资源。我可以去帮你打听,保证你儿子安然无恙。可是,……”说着,周娜的声音渐渐低下来,高傲的头颅也垂下来,晶莹璀璨的眼眸里似乎有点点泪光,仿佛灿烂星河里最亮最动人的那两颗星星。
“娜娜,我……”李万翔不知怎么的,也许是受了这夜色的蛊惑,也许是美人垂泪的动情,也许是儿子突遭不测的打击,一时间起身紧紧拥住周娜,“请你,”他用力地说出这两个字:“一定要帮我解救我儿子!事成之后,定有重谢!”
“你知道我不是图你的重谢!”
“……事成之后,我们就结婚!”
李万翔趁着周娜到洗手间打电话的空当,一个人瘫坐在真皮沙发上,轻轻闭上眼睛,所有的情形像过电影一样,一帧帧在脑海中浮现重组。
吴德仁、吴晓仁、朱甘强、徐林生、周娜,他们的脸就像万花筒一样在眼前打转,吴德仁看房的时候因为无人陪伴失足掉下电梯轿厢,吴晓仁得到了巨额赔偿决定撤诉,朱甘强作为徐林生的相识战友出手相助,周娜虽然怀孕了却对自己依旧有情,在儿子被绑架的危难时刻助我一臂之力。
李万翔长长地叹出一口气,“天不亡我!我一定会有路可走。”
在巨大的变故和重重压力之下,他觉得自己做出这个决定英明万分,林秀娟虽然好,但那种好,说不出个名堂。进,不能多一分利,退,不会少一毫益。她的好,就如同她的面容,温吞乌苏,轮廓黯淡,模糊不清,让人看了之后不会再看第二眼。
而且眼下这个档口,周娜能帮自己解决大问题,和她结婚,又能免去对方以怀孕挟持自己的危机。——李万翔觉得自己做了一笔稳赚不赔的生意。
是的,生意!李万翔想起这两个字就有隐隐的自豪。从那样的寒苦卑微出身,发展到如今的动辄千万身家,全凭自己的生意头脑。跟任何人打交道,做任何事之前,李万翔都能盘算几分,孰轻孰重,获利几分,亏蚀几厘。估摸着下来,与最后实际成交都相差无几。
商海浮沉二十年,李万翔觉得自己已经练就了金刚不亏之身。雁过拔毛虽算不上,凡经手必获利已经是颠扑不破。
所以,我不会输的,想到这里,李万翔的嘴角浮出了一丝迷之笑容。
打完电话走进办公室的周娜,看到这一丝笑容也有一瞬间的迷惑,她不知道对方,这个年仅不惑之年的中年男子怎么会如此淡定,居然在这个节骨眼,还能笑得出来。
她像只猫一样,轻轻地走近万翔,两个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直到周娜站在他的面前,李万翔好像还神游天外,半天没回过神来。猛地一抬头,看见周娜的身影,才反应过来。
“万翔,你看这是谁?”周娜递过手机,让对方看屏幕上显示的一张照片。
李万翔扫了一眼,就惊喜万分,仿佛身体注入了兴奋剂,忍不住微微地痉挛起来。
“是高梓!我儿子!”一张像素模糊,远远地看不太清的照片,只依稀看得到一个小男孩骑在旋转木马上,似乎很开心。
“我哥哥说了,你是我的朋友,就是他的朋友。我答应了要帮你把儿子找回来,就是他答应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不知什么时候,周娜已经轻移莲步,不动声色地坐在李万翔旁边。一阵熟悉而又诱人的香味,远远近近地飘荡
在空气中,氤氲缭绕。
“娜,”李万翔一把抓住对方的小手,“我们结婚吧!你对我太好了……”
谋略规划许久的计策眼看着近在咫尺,周娜却突然有些不真实感。“万翔,我,我,还没考虑好。”
“还考虑什么?我们马上就领结婚证,办婚礼,我要给你一场最盛大、最排场、最阔气的婚礼!”
“那她呢?”
“她?”
“林秀娟!”
“哦,这个好办。我早就拟好离婚协议,打电话让她来签字就行。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周娜细细听下来,李万翔要给林秀娟一笔不菲的补偿金和一套房子,还要把儿子留在自己身边抚养,心下隐隐地有些不快,又听对方的意思要签署婚前协议,财产各自独立,就忍不住要翻脸。
谁知李万翔仿佛看破她的心思,连忙说:
“娜娜,你不要担心。我跟你的婚前协议,只是做给别人看,不要让别人以为你是为了我的钱跟着我。我们一结婚,我就把公司转到你的名下。这样,你不就是名正言顺的老板了吗?连老板娘这一步都省了!”
周娜暗暗窃喜,一种胜利感油然而生。二十出头的如花年纪,就拥有千万家业,说到哪里去,自己也不失一个成功者。
双方谈妥,皆大欢喜。周娜让李万翔看了一段儿子的视频,视频中,李高梓歪着小脑袋,打着瞌睡,一边睡眼惺忪,一边小声嘀咕:我要妈妈,我要爸爸!
看到这里,李万翔心乱如麻,连忙应声道:“娜娜,快点,快点,告诉你哥哥,我和你马上就结婚了。这就是自己家孩子,让他马上救人!”
“放心,我哥哥已经找到朋友的关系,今晚十点在杨家大桥下面716公交车站接人!”
周娜离开李万翔的办公室时,正是李万翔给林秀娟打电话,让她马上赶到自己办公室的档口。
听着李万翔的语气,周娜心知,一切稳操胜券,于是,她放心坦然地转过身去,留给李万翔一个黑天鹅般的背影:优雅、高贵、不可小觑。
听着自己的高跟鞋踩在写字楼的地板上,发出轻轻的“哒哒”声,看到自己如同天鹅颈一般修长挺拔的脖子,支撑着自己高贵的头颅,倒映在晶亮的玻璃门中,那种与生俱来的美艳绝代仪态万分,仿佛都在告诉周娜一个声音:你赢了!
二十四、人生不见,与君诀别
方柏阳没想到,自己在从老家县城到魔都的大巴车上结识的一位老乡,居然起了这么大作用。
当他带着李高梓去比萨店吃饭时,吃到一半,方柏阳对李高梓说,叔叔去个洗手间,于是黄鹤一去不返。然后,他的老乡就开始登场唱戏了。
和方柏阳文弱书生的气质不同,这位老乡面相老气,装扮一言难尽,尤其是眼睛嘴巴透着一股行走江湖的匪气。李高梓虽然十岁,可平时见的人都是父慈母爱,老师和蔼,朋友亲密,哪里见过这个阵势。
当他听到这个凶相毕露的家伙用低沉的声音命令道:起来,跟我走!
李高梓吓得都要尿裤子了,连忙起身,把自己含在嘴里的半块鸡肉囫囵吞枣地咽下去,直咽得他翻白眼。又听见
对方说:不许乱哭乱叫,否则我饶不了你。
听到这,李高梓就像着了魇魔一样,乖乖地背起书包,含着泪,低眉顺眼地跟着这个男子,上了一部不起眼的破车。
上了车,这家伙就缓缓地开着车,黢黑的脸庞,阴郁的眼睛,四处扫描。李高梓坐在后排,不敢哭不敢叫,一泡尿早就打湿了裤子,没开空调的车厢里,冰冷刺骨的棉裤,让他体会到从未有过的恐怖。
等到车子晃悠晃悠着,时间长了,紧张恐惧的心态渐渐让李高梓变得麻木。他靠在后背上,朦胧欲睡的同时,还在抽泣:我要妈妈,我要爸爸!
李万翔看到这段令自己肝肠寸断的视频,正是由这个老乡发给方柏阳,方柏阳转给周娜的。
李万翔看着周娜离去的背影,忽然升起一丝说不出的感觉,具体是什么,他也说不上。只是看着那个曾经毫不起眼,默默无闻的黄毛丫头,一转眼就变成了一位风姿卓越,仙气飘飘的人间尤物。她转身的背影那样决绝,离去的脚步那样轻快,那种骨子里流淌的喜悦似乎藏不住,李万翔放下电话,有些踌躇,但是,这种感觉很快就被林秀娟的哭声驱赶走了。
话筒里传出的声音,老气苍白而空洞无力,这就是他的妻子,十二年的枕边人,李万翔仅存的一点内疚感就消失殆尽。
“是时候做个了断了!”李万翔喃喃自语,全然不顾四周寂静一空,没有灯光,玻璃幕墙透进对面的霓虹灯光,喑喑哑哑流淌在桌子上,沙发上,电脑上。
林秀娟从接到李万翔的电话,到站在李万翔的办公桌前,花了一个小时。因为闹市区的晚高峰,堵车堵得厉害,导航上全是橙色拥堵,甚至有几个路口呈现红色——严重堵塞。
但是林秀娟的内心,依然是快乐着的,甚至有几句哼出的歌曲,她觉得上天对自己太好了:老公昨晚良心发现,今天一天对自己都那么好;儿子不慎走失,两个小时就找到了;自己才三十六岁,一切重新开始,都不晚。生活真的太美好了!
可是所有的美好都在她站到李万翔的桌前戛然而止。
她接受不了,可是不得不接受。因为人生不可能拒绝自己的天命,要知道,命运之神有时候很仁慈,有时候却又特别严格。
眼泪已经哭干了,额头的皱纹增添了几条,法令纹更深了,衣服上的褶皱比人还显得老气,——罢了!林秀娟掠了掠自己散乱的头发,从口袋里掏出一根陈旧的皮筋,把散乱的头发扎成一个丸子,慢慢从地上爬起来,然后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尘,抻了抻上衣裤子。做这些动作的时候,林秀娟始终没有正眼看过一眼李万翔。
吾意已决,何必苟求。
林秀娟从李万翔的金黄琥珀笔筒里随便捡了一支笔,在离婚协议上一笔一划地签上自己的名字:林秀娟。三个字在灯光下仿佛淌着泪,总是离人泪!但是,在不爱你的人眼中,这泪水早已不是弥之珍贵的宝石,而是令人唾弃的鱼目。
李万翔略略有些惊讶,他不明白,这个被自己视作最懦弱最无能之辈的女人,怎么会突然间如此勇敢。谁给了她勇气?不过转念一想,自己不是一直觉得要林秀娟答应离婚是件头疼的事吗?不是一直担心对方一哭二跳三上吊吗?眼下,她这么爽快地签字了,不是正随自己心意吗?
看着林秀娟递过来的离婚协议书,李万翔也毫不犹豫地提笔签字。因为对方还没有完全松口放儿子呢,留给自己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妹妹这么掏心掏肺地对你,你要是负了她,我绝不饶你!”他得赶紧把正事办了。
从林秀娟的角度望过去,四十岁的李万翔头顶头发稀薄,已经有些秃顶的趋势,尽管他拼命掩饰,把周围的头发往正中间堆积,使别人看上去不那么突兀,但真正熟悉的人都知道他的头发早已往“地中海方向”发展。
目光再往下走,林秀娟看到李万翔的小肚子微微腆起,活像怀有四、五个月的身孕。坐在沙发上,人整个塌陷进去,签字时,突出的那一块让人硌得慌,显得格外笨拙。
林秀娟忽然一阵凄惶,仿佛茫茫人海无限汹涌波涛骇浪中,有个人牵着她的手,朝前走,不慌乱不走神,心里特别笃定。突然间,那个牵着她的手的人,说走就走了,连个“再见”也没有,连回头望一眼的程序也省掉了。
只剩下自己,站在天地间,眼巴巴地看着牵手的人松开自己的手,牵着另一双柔滑纤细的手,头也不回,兴高采烈地朝前走。而自己,这个年近不惑的半老徐娘,谁不会多看一眼,就傻傻地一个人站在那里,直到海枯石烂天荒地老。
林秀娟不忍再想,她趁着李万翔低头签字的那一会,认真地把自己的脸,嘴角,眼睛揩了遍,然后,昂着头,始终不再多看对方一眼。直到最后,说了一句:“我要见儿子一面。”
说完,扭过头去,径直朝门口走去,只留给李万翔一个背影。李万翔忍不住问了一句:“哎,你去哪?”
“我回家,把自己的东西整理好。今晚就搬出来!”
“明天吧,明天再搬。晚上十点我去接儿子,你可以和他多呆一会……”
话音未落,只听到“嗒”一声,林秀娟的身影已经消失在门禁处。
一个小时内,李万翔送走了生命中两个女人的背影,一个轻快明媚,婀娜多姿,一个沉重笨拙,身影发福,前者走向自己生命的巅峰,而后者却一步步挪向生活的深渊。自己的决定是对是错,将来是福是祸,谁能知晓?
林秀娟走出李万翔办公室,看见磨砂玻璃门外的景象,不禁有一种重生的感觉,进去时还是一家三口之主,出来就已经成为孤家寡人。林秀娟想哭,但是环顾四方,发现格子间里还有几个加班没回家的员工,正低着头假装工作,其实耳朵竖得尖尖,正想打听老板前后跟两个女人都谈了些什么,她忍住了。反而面带微笑,冲着曹月丹:“丹丹,我们回家吧!”
懵懵懂懂的曹月丹一屁股坐在副驾驶座上,就问:“咦?舅舅呢?怎么他不跟我们一起回家?”
“他还有工作,晚点回来。”
“哦~”
一直到家中,林秀娟没有多说一个字,曹月丹似乎也看出舅妈神色不对,不敢多言。看到家中连灯都没开,饶是心再大,曹月丹也想到一个人,“高梓呢?豆豆呢?(高梓的小名)怎么这么晚还没回家?舅妈你下午不是去接他了吗?怎么这么晚还没到家?”
林秀娟背对着她,低声说:“你舅舅让人接走了,现在别人家玩着,开心呢!”
待到曹月丹终于歇口气,闭上嘴,在二楼夹层的小房间里睡着了,林秀娟这才敢关上主卧房门,熄了灯,一个人斜倚在床头,静静地看着四周一切:楼高三米,房间长七米,宽五米,一间主卧,放了一张大床,还有一个衣帽间、洗手间,加起来总有五六十平米吧。再看绛红色缎纹窗帘,没有灯光也能看到欧式鸢尾草的花纹;窗前一个落地雕花瓷瓶,里面装满了林秀娟从前在花店里淘回来的各色银柳,还零散地系着小小的红灯笼;这边两个床头柜,对面是电视柜加超大屏幕的电视机,左边床头柜里还放着一瓶李万翔的胃药,右边床头柜里还有自己的针线包。
就是闭着眼,林秀娟也能准确无误地找到家中所有用具存放的地方,老公儿子婆婆姐姐自己爸妈脾气性格如何、日常生活需要准备什么,都如数家珍,一日三餐大家要吃什么,睡着了都能盘算开。
可现在,所有人都不需要这些了。没有人在乎她的劳动,没有人在意她是否还在,没有人问一句她将来怎么生活,没有了,没有了,——想到这里,林秀娟再也忍不住,用羽绒枕头堵住自己的嘴,一个人,在黑暗中,尽情恸哭。
二十五、有匪君子,如切如磋
邹辉一走进这个小区,就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宽敞气派不说,绿化植被幽深,奇花异草居多;小区中间一个人工水景台,周边一圈全是大理石雕刻的天鹅,或展翅欲飞,或悠扬引颈,俗称“天鹅湖”;再往前走,就有高低起伏,地势变化,也是人工修成的,低处是私家车库,高处则是各式楼房。
小区挺大,有平层,有叠加,有复式,还有小型别墅,只看得邹辉眼花缭乱,手里拿着手机,半天也导不出个所以然。好不容易,来到一个单元楼梯口,正好就是自己此行的目的地:“5幢120号602”。李万翔家是一套六复七的复式楼。
邹辉走到楼道门口,正当中是密码门禁,两旁是锃亮光洁的门洞,擦呱啦新(崭新的意思),可以照得见人影,足见小区物业之高档。邹辉望着镜子里自己的模样:年方三十二,身高一米八,身材魁梧,长相正常,眉宇间一股英气。
我是一名人民警察!邹辉握着拳头,暗自对自己说,我要对得起父亲传给我的衣钵。从小没有父母长辈指点的邹辉,在人情世故方面缺少悟性,只知道凭借一己之力独自前行,如今遭此打击倒也把那股桀骜不羁恃才傲物的脾性慢慢收敛许多。
经过昨天一整天的反思,他决定申请调到另一个分队,可上级还没有回复,于是邹辉提出公休一段时间。朱甘强正好乐得眼不见心不烦,做个顺水人情,给他多放几天假吧!省得这小子添乱。
邹辉表面上风平浪静,不起波澜,心里却没有丝毫放弃,他决心利用这段时间,对这个案子私下里进行侦查。
一早起来,邹辉找邻居家借了一辆电瓶车,穿上外公以前留下的一套工作服,往电瓶车后箱里放上一套水电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