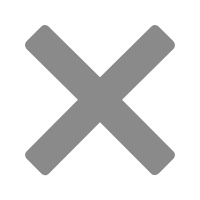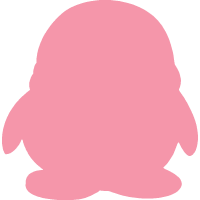第 6 章节
个瘪嘴阿婆。
“哼,这也说不定,老板有没有包二奶,还会跟你说?你是哪只眼睛看到他没有小情人的?据我所知,李总可是有个金屋藏娇的小美女哦!”卫华不以为然地摇头说着,
“啊?!不会吧?不会啊!”几个花痴的女孩子惊呼起来,她们边说不可能,边把脑袋凑得更近了,个个饭也吃不下了,就想听听卫华进一步爆料,“卫姐,你说说看嘛!到底是什么样的小美女啊?”
金艳琴不服气地瘪瘪嘴,“你凭什么说老板有情人,是你的左眼看到了,还是右眼看到呢?”
卫华轻蔑地一笑,仿佛她的问题不值一提,“我只能说,这个女孩是个90后,而且是舞蹈系的高材生。这个料够猛吧?”
金艳琴刚想提高声调继续抨击卫华的话,就听得白晓丽把筷子重重一放,用她那好听的声音不急不慢地说:“你们够了吧?背后议论老板,是不是都不想干了?”说完,白晓丽端起不锈钢餐盘,起身快步离去。
剩下几个八卦女坐在那里,面面相觑。气氛沉闷了几秒,很快被卫华打破了,“呵呵,人家正宗大老婆都没跳出来呢,她倒跳出来现眼。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货色,不就是个小秘书吗?是不是自己暗恋老板,听说人李总有了情人,一时之间接受不了?难怪成了黄金剩斗女!”
“就是啊,凶什么凶?李总都没这么凶的对待我们呢,她算哪门子管理人员?”“卫姐,再跟我们说说呗,”“对呀,说说,我们最喜欢听这个了,”
“说说可以,想听的就坐在这儿继续听。不想听的,就请移动大驾,换个地方。”卫华边说,边斜瞄着金艳琴。白晓丽离开,金艳琴一下就被孤立了,看着几双眼睛直直地盯着自己,二十岁的女孩终于顶不住了,红着眼睛,饭也没吃完就气咻咻地跑掉了。
白晓丽坐在办公桌前还在生气,不争气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她和李万翔的办公室是个套间,李万翔的办公室在里面,她的办公桌就摆在外面的房间里。任何人进入李总的房间,都要经过她的桌前,而她,自从二十岁进入高翔公司以来,已经在这里度过了十五年的光阴。
十五年,二十岁到三十五岁,一个女人,最美好的时光,白晓丽全部奉献给了高翔公司,或者更确切地说,全部陪在李万翔身边。早上七点起来,八点半到公司,打扫李万翔的办公桌,替他泡好茶,将需要签字的文件帮他整理好,已经签发的文件转达各部门,订酒店、买机票、招待客户、清理垃圾;他有个头疼发热胃痛便秘,不想去医院,她连忙递上小药箱里的药;他有个加班出差开会投标,她就会不眠不休一直开着手机或等在办公室里,直到他平安回来。他笑,她一起笑;他怒,她比他更急;十五年来,白晓丽早已习惯这种生活节奏,在心底,她早已把李万翔视作自己最理想的爱人,至于对方知道与否,根本就不重要。只要她自己活着,爱着,就够了。
其实,早在一年多前,白晓丽就看过周娜的照片。
平时,李万翔的物品隔天就要她收拾一次。可那段时间,白晓丽发现李万翔不怎么让自己碰他的东西,实在脏乱了,也都是自己动手收拾,就有些奇怪。
一天下班后,白晓丽假装忘记拿手机又折回公司,发现李万翔已经走了,而自己有他办公室的钥匙。打开推门进去,他的桌上茶几上放着一些没有收拾整理好的文件票据纸张。白晓丽沉吟再三,鼓起勇气帮他收拾起来。除了一些□□文件和写过的废纸,白晓丽倒也没发现什么特别之处,可当她收拾完毕最后巡视一遍房间时,不经意看到李万翔的抽屉忘了上锁。鬼使神差地,白晓丽拉开了第一个抽屉,里面有一个笔记本,都是工作笔记。翻了几页也没啥花头,正要放回去,却有一张照片从里面滑落。
白晓丽扫了一眼,用几乎颤抖的手拿起来凑近了看:一个女孩子正站在李万翔身边,形同情侣。两个人迎着风,身后是万丈金光,漫山遍野的青山绿水。说不出有多美,但是,那脸青春逼人,那笑没心没肺,眼角连一点褶皱都没有,长发飘飘,白衫胜雪,看上去就是一对璧人。白晓丽见过林秀娟,知道这不是李万翔的老婆,知道他没有异性朋友,即便有,他也从不会拍这么亲昵的照片。
白晓丽一屁股坐在李万翔的大班椅上,泪水一滴滴滚落在照片上,良久,还是抬手细细地揩去。这之后,白晓丽装作什么也没发生,该干嘛干嘛,也没有跟任何人提起,好像这一切凭空失忆了一样。她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是,即便生气,那也是林秀娟的权力,还轮不到她白晓丽。
可今天卫华的几句话,不知触怒了白晓丽哪根神经,让她蓦地火冒三丈,出离愤怒,好像她们在说自己的老公出轨一样,她走到哪里,总感觉有人在背后戳自己的脊梁骨。白晓丽愤愤不平地坐着,“这群三八婆!”她忘了自己是谁,和李万翔的关系是什么,十五年来李万翔和高翔公司已经融入她的灵魂,令她产生一种强烈的代入感,她觉得自己该做点什么。
她拿起手机想发短信,又觉得写不尽心中的感受;想打电话,又怕被人听见;让她当面去找李万翔谈,她有没这个胆量。思考半天,她决定写一封邮件给李万翔。从十五年前写起,告诉他,自己从二十芳华到如今青春已逝的半老徐娘,十五年来的每一天,都是如何度过的。告诉他,只有自己,是唯一忠诚不渝一片丹心为他好的那个人。
白晓丽本就是文案高手,午间休息的一个小时,她神情凝重,不苟一笑,眼睛直视电脑,“噼里啪啦”打好了近一千字的邮件,最后的结尾,白晓丽思酌良久,落笔生花,十分满意:
“你曾经对我说:
‘如果,
你真的肯把整个人生放进去,
这个世界也绝不会亏待你。’
你不知道的是,
我的人生,
一直都放在你手里。”
可是,为了究竟要不要发给李万翔,白晓丽纠结了好久,眼看着同事们陆陆续续打开电脑开始下午的工作了,再不发,一会就有人来找自己。白晓丽咬咬牙,闭着眼睛点了“发送”键,等睁开眼,邮件已经发送成功,想撤销也已经来不及了。
“行了,听天由命吧。”白晓丽用只有她才能听见的声音说给自己听。
李万翔本来有个午后小憩的习惯,但今天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他坐在大班椅上转来转去,继而又踱到窗前。看了许久,直到午后的阳光刺在眼中有些发毛,视野中的万物似已成沧海桑田,他才慢慢转过身子,准备喝点茶。
突然听见手机“叮”一声响,有新的邮件进来,一向矜持拿架子的李万翔也顾不上形象,飞奔到电脑前,进入邮箱,打开收件箱,却是白晓丽的一封邮件,李万翔花了两分钟扫视了一遍整篇文字,读来心中却百感交集。
李万翔何尝不知白晓丽的心思,当初公司初建之际,是他亲自面试的她,录用她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她对薪水没有要求。可后来,李万翔看到她一个女孩子,貌不惊人,却独立好强,对工作尽心尽责,对收入毫不计较。很多次,李万翔早上七点半到公司,发现白晓丽已端坐在桌前,手里不停地忙碌着,一问,才知道,她一整晚都没离开公司。有时候是整个通宵加班,有时候是忙得太晚,就睡在沙发上不回家了。
最初,李万翔并没有对她留下什么印象,慢慢地,就开始留心她了,暗地对这个精力过人,对公司的热忱在某些方面超过自己这个老板的女孩钦佩不已。眼看着白晓丽那么单薄瘦弱的身板没日没夜地为公司操劳,李万翔也明里暗里开玩笑让她多陪陪自己男朋友,或者笑问她要不要帮忙介绍老公,但都被白晓丽黑着脸严词拒绝了。
这一拒绝,就是十五年。
公司员工走了一拨又一拨,办公地点也从最初的地下室到商住楼,后来又搬到这顶级的写字楼里,连李万翔都改变了很多,唯一不变的,却是白晓丽:黑瘦、戴黑框眼镜、不苟言笑、办事雷厉风行、永远不谈私生活。她已经成为高翔公司的一道风景线,公司许多人私下都在议论纷纷,说什么白晓丽是同性恋,也有说白晓丽实际是李万翔的生活秘书,还有说白晓丽曾经遭受生活巨创,所以看破红尘心如止水云云。
这些话,李万翔都知道,白晓丽的心思,他也渐渐明了。再不明白,不是傻子就是疯子。李万翔不是没有爱的能力,但是,对她白晓丽,实在没有爱的冲动。人与人之间,是个奇怪的气场聚合:一旦缘分对上了,天雷地火勾魂摄魄死生契阔不离不弃;如果没有缘分,无论对方为你做什么,哪怕付出生命,却也只有“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何况,眼下,李万翔的心不在此。他选中白晓丽的邮件,点击“删除”,眼都不眨一下,轻轻按下鼠标,白晓丽连同她的邮件,就在李万翔的心里永远删除了。
十五、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朱甘强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手里把玩着手机,心下琢磨着怎么告诉李万翔事件的进展。他本想早点告诉李万翔案件已结案,自己已被宣布接任王队,成为朱队;可转念一想,又不准备马上告诉对方,否则李万翔会觉得这事情办得太容易了,现在就该让他心
急如焚,否则他怎么肯轻易兑现自己的承诺?
两个小时前,当邹辉把自己的鼻子一拳击到鲜血直流,随后去了单位医务室简单包扎一下,朱甘强仍然喊着后背的脊柱痛。也难怪,刚刚他被邹辉打倒在地时,后背正好抵在桌子的尖角,借着那股冲力,直戳在脊柱的凹陷处,说痛一点也不过分。
几个同事又连忙驱车把朱甘强送到医院,拍片,CT,一阵忙乎。
这期间,王队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差不多两个小时,其间打了若干个电话,说了满满一箩筐的话。当他带着满身烟味和一脸的憔悴走出办公室,看得出他的内心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煎熬和反复权衡。王队走到办公区,看到邹辉的背影,一个人坐在那里,似乎正在翻阅着一沓资料。本来魁梧身材乍一看去,此时却略显落寞、蕴含着一种无声的爆发力。
王队在心里默默地叹了口气,走过去,拍了拍邹辉的右肩,坐在旁边的凳子上,正欲开口,就看见邹辉猛地抬起头,“王队,你什么都不用说。我都明白……”
“你明白什么?你明白个鸟!”邹辉不说则已,一说话,王队就像点燃的炮竹,狠狠地一拍桌,桌上的水笔、本子弹起来,有两张纸条趁机飞舞,半天才落下。他“砰”的一声站起来,看了看邹辉,又坐下。
“有没有去医院看看老朱啊?”
“没有。”
听闻此言,王队恨不得给邹辉几拳头,硬是给忍住了。邹辉于他,就像自己的儿子一般。王队儿子早夭,白发人送黑发人,他心中的苦痛多年不得排解。看到邹辉,和儿子年龄,身高,脾气相仿,心中油然一种亲切感,眼下这种心情正属于父亲之于儿子“恨铁不成钢”的情感交集。
“一会散了会,你和大家一起去看看老朱。”
邹辉抬起头,“散了会?什么会?”
王队没有回答,只是看着对方,一双眼睛里饱含了焦灼、严厉、惋惜等等百味杂陈,然后慢慢站起来,用低沉的声音通知大家到会议室开个会。
只有十五分钟,会议结束。邹辉走出办公室,同事们都纷纷相约着去医院的去医院,去办案的办案。大家窃窃私语着,交谈着,与邹辉擦肩而过,看到他聛睨一切秒杀全场的表情,谁也不敢多招惹他。
王队几个大步追上邹辉,拍拍小伙子的肩膀,胡子拉碴的脸泛出一丝少有的笑容,用略显沙哑的嗓音说:“小伙子,跟我上车,去看看老朱,他现在是你们的朱队长了。”
邹辉稍有迟疑,王队狠狠地给他一捶子,“还不快点?”
一路上,两个人,沉默无语,良久,王队开口了:“小邹,下周开始,我们不在一起共事了,希望你能好自为之。很多时候,我们会做事情,更要会做人。我是过来人,以前也吃过这方面的亏,所以不希望你也重蹈我的覆辙……”
“王队,你说的话,我记住了,我明白,你是真心为我好。但是我这个人,”话到此,邹辉突然有些顿住了,他知道,这个时候的王队,已经不再是以队长身份讲话,而是以一个父亲的身份在谆谆告诫自己的孩子。
车玻璃外,满世界里的人在熙熙攘攘的街上来回穿梭,红绿灯闪烁不停,路中间还站了个执勤的交警,但仍然拥塞不堪。正值冬日,每个人表情都是那么冰冷木讷,默然无奈。邹辉看着这一幕幕,忽然涌起一种愤懑欲要挣脱却是不能的悲哀。真心给予他父亲一般的爱护,千万人的大都市中,除了王队,还能有谁?如果此时他还要继续“但是”后面的话,岂不要伤透他的心?
于是,邹辉停住了,没有继续刚才的话,而是把眼光投向窗外的一幢幢摩天大楼,深蓝色的玻璃幕墙倒映出一个个身影,邹辉仿佛也看到了自己:三十出头,还是愣头青一个,未婚,无房无车,除了拼命三郎的气场,一无所有。想到这,邹辉倒笑起来,咧了咧嘴,其实是想拼命忍住已经要落下的眼泪。
一旁的王队轻轻地拍拍了座垫,想说什么,又什么都没说。
时光在这里走向下午的四点:王队升迁,调离刑侦队;朱甘强接任,成为朱队;邹辉?还不知道未来的命运;李万翔终于接到朱甘强的消息,案子终将结束,昨日已成为一场浮云;林秀娟度过了平生最平静,最甜蜜的一天,日后她回想起来,总觉得这甜蜜里多少隐含着不安;周娜,则是平生最忙碌的一天,因为她的千万富翁计划,即将登场了。
昨天夜里,周娜和方柏阳细细叨叨说了大半宿。到了凌晨,两个人各自暗怀鬼胎扛不住困意,终于斜躺在雕金绣银的大床上沉沉睡去。中央空调温暖适宜,微微地吹出新鲜空气,让人好像躺在一望无垠绿草如茵的大草原上,目之所及,全是绀碧的天空、丝绸般白云、满地遍野的野花杂生,还有一抔湛蓝的湖泊,嵌在草原中间,仿佛母亲温柔的眼,将孩子般的她轻轻呵护。
周娜就在这样的半梦半醒间,看到自己的母亲,母亲一直身体不好,总是一副病怏怏的模样。可在这梦中,周娜看到母亲又恢复了年轻时代活泼俏丽的样子,只见她微微一笑:
“娜娜……”
周娜使出最大的劲,想张开嘴答应妈妈,可是怎么也动不了,仿佛肌肉被强力黏剂粘住了一样。
“娜娜,你年纪不小了,早点找个可靠的男孩子,定下来。我和你爸就放心了。”
周娜拼命想点头,无奈身体像被魇住一般,纹丝不动。
“妈身体不好,就想早点看到你和哥哥早点结婚,你哥早点抱孙子,你呢,我就盼着嫁个好人家,开开心心地过完这辈子。你妈我呀,这辈子,没别的想法,只要你们过得好,我就是死了也没什么挂念的……”
说话间,周娜看见母亲的脸像是被大雪融化了一般,慢慢地,一点点地,开始模糊起来,到最后,竟变得完全消失殆尽。
周娜几欲挣扎却又感觉身体像被大磐石重重地压在心口,她开始张嘴喊叫,终于喊出一声:“妈妈!”
一刹那间,所有模糊梦幻的景象全都像泡沫被刺戳破一样,毛乎乎的边缘都变得清晰起来,只是周娜浑身冷汗,四周一片漆黑,仿佛伸手不见五指,母亲像是从未在梦中出现一样,一切静得只听得见方柏阳的鼾声。
周娜没有叫醒方柏阳,倒是自顾自地拿起一方真丝绣花靠枕,右手轻轻抚摸着绣花凸起的针脚,和柔软的流苏,左手放在胸口,她听到自己心脏“咚咚”地跳着,她知道,自己的这场戏无论如何都得演下去,因为开弓没有回头箭。
“妈妈,你等着看,女儿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同一个夜晚,还是这片寂静天空下,还有一个母亲也彻夜不眠。
泼墨一样的暮色像一张大网紧紧罩在城市头顶,月色早就消失在晶莹如玉的雪粒里。魔都潮湿而阴冷的冬季,让西北角的一个破旧小区里,倍感寒气逼人。
这是老城区一片还没有拆迁的老公房,逼仄的楼道,斑驳的墙壁,昏暗的路灯,到了晚上基本没有什么路人。
吴晓仁和母亲就住在这个老公房里,眼下,母亲炒了一碟花生米,买了半斤三黄鸡,备了两个小菜,倒了一杯黄酒,放在儿子面前。
“侬快点吃,吃完我要打碗!(洗碗)”
“晓得了,老太婆哪能嘎西多花头!”
吴晓仁的妈妈听了这话,反而笑了。年近四十的儿子一直单身,娶不到老婆,最近双喜临门:邻居叶阿婆介绍了一位外地来魔都打工的小姑娘,比自己儿子小了17岁,“模样老嗲额,手脚又灵光,伊爷娘讲过了,这个媳妇就送给你当女儿啦,伊屋里厢又冇啥负担,爷娘也拎得清。侬讲讲,这笔买卖划算吧?”
“划算,划算,叶阿婆介绍的笃定不会错!”
上周吴晓仁跟小姑娘见过面了,很满意,自己就放心了,只管催着儿子早点把结婚仪式办了,就等着抱孙子了。
可是结婚就得要买房子,自己家的老头子是个一辈子帮人做点装修工程的小包工头,有点钱就吃老酒,再不就出去赌老虎机,不仅没有攒钱,还欠了外头10万元。10万块,对于他这个家庭来说,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这个死老头子!”现在想起来,吴妈还是恨得咬牙切齿。
所以,乍一听吴德仁从电梯空厢里失足摔死的消息,自己心里居然有一种说不出如释重负感,当然,只是一刹那。很快,她就清醒过来,老头子这一死,欠了一屁股债,谁来还?儿子都快四十岁了,工作没个正经工作,成天游手好闲,还没结婚,后半辈子靠谁呢?
一盘算,吴妈跟儿子一合计,两个人就摸索着去“在水一方”售楼处大吵大闹,寻思着这么大公司,总要给点封口费。只是没想到,这个李老板这么大方豪爽,手一挥就送了一套公房给他们。
“早知道老头子这么值钱,我就不应该那么轻易答应他。再让他给一套房子,阿拉后半生就发财了!”吴妈边想着边喃喃低声说了出来。
“哦呦,好啦,人不能太贪心。侬想想看,阿拉爷是怎么死的?伊为啥要去‘在水一方’看房呢?迭种高档楼盘怎么轮到阿拉去看呢?”
一语敬破吴妈,她愣住了,不禁脱口而出,“侬啥意思?难道侬爸爸是被人害死的?”
“是不是被人害死的我不知道,但是这种大老板,我们这种小老百姓是惹不起的,拿到这套房子老好了,我老开心了!所以姆妈,侬就不要多想其他了!”
“呵呵,侬有媳妇了,出息了,教训起老妈来了。我当然清楚了,有这套房子侬结婚我就不操心了。”
见吴晓仁不吭声,她又继续喋喋不休,
“哎,伊个小姑娘哪能?侬还满意吧,以后会对姆妈好吧?”
“会的,会的,姆妈侬放心。”
吴晓仁呷了一口温热的黄酒,夹了一筷子鸡肉,放在嘴里细细咀嚼起来,虽然百事不成,但他还是个美食家,细到骨子里的美食家。所以,当他一看到父亲在那密闭空间里,血污四溅、面目狰狞的样子,简直要让他把早上吃过的小汤包一口呕吐出来。他强忍了很久才咽回去,对父亲的尸体不忍再睹。倒不是因为痛心,而是实在无法忍受这种视觉和心理上的冲击。
眼下这样的结局,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解脱。
“老头子,侬放心,吾同姆妈一定会好好过日子,等阿拉结婚了,我带媳妇孙子一道来给你扫墓。”
想着,喝着,夜色更浓了,吴晓仁觉得眼前渐渐模糊起来。整个城市都要睡了,这些日子大家都累了,是时候放下了,大家都能功德圆满,皆大欢喜,想想就开心。
吴妈也抿了一口小酒,哎,苦了大半辈子终于苦尽甘来,儿子要娶媳妇了,老头子死了死了还是给我们挣了一套房子,剩下的日子就好过咯!就这样构思着美好的未来,吴妈禁不住笑出声来,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魔都号称是不夜城,你看那夜色笼罩下的屋脊起伏线,怪石嶙峋,奇峰异景,张牙舞爪,暗藏玄机,无数人从这里飞黄腾达,可更多的人却是一个不小心就掉在这无底深渊里,永无出头之日。
十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虽然低着头,李万翔用眼角的余光看到有个身影在门口晃悠了一圈,很快又不见了,心下知道是谁,也不说破。
白晓丽在门口转来转去,还是希望李万翔喊她进去,能够当面问问她那封邮件是怎么回事,哪怕指着鼻子大骂她一顿,也不辜负自己这十五年来的苦苦相思之情。她甚至靠在椅背上遐想起来:李万翔看了邮件,又怒又喜,拍了桌子喊自己进去,暴跳如雷地问她究竟什么意思。而她白晓丽,终于可以坦然面对对方侃侃而谈,一诉衷情,声泪齐下,竟而把李万翔感动到眼圈泛红,深情款款地凝视自己半晌,慢慢走向彼此,最终两人深情相依相抱。
但是没有,等了又等,里面的办公室没有半点响动,就连门口的那棵青翠的发财树似乎也招了两下手,白晓丽以为自己看花了眼,忍不住揉揉了眼睛,定睛再看,却是一点没动静。几次手痒痒想看看邮箱又不敢,可是两三个小时过去,看看李万翔是不会当面和自己谈这个问题了。“也许,李总羞于当面和我说自己的心理感受,也许,他和我一样,有满满一肚子话要对我说呢?白晓丽,勇敢点,看看邮箱吧!”
说完,白晓丽片刻也等不得,点击鼠标就进入收件箱,她怕自己再犹豫就真的会崩溃,用颤抖着的手点开“收件箱”,她焦急地扫描着新邮件,可是——没有,没有来自她梦寐以求渴望祈盼的那个地址的邮件,白晓丽的手不抖了,无力地,缓缓地滑下桌面,垂在扶手旁。
他不可能没看到,因为我平时发的每一封邮件他都会以最快的速度反馈,但是这一次,既没有回信,也没有当面说起这件事。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对方根本不想不愿和自己谈起这件事。我本来就应该知道有这种结果的,我本来就应该有自知之明的,我本来就应该想到我和他不可能有故事的。白晓丽,你都三十五岁了,还这么幼稚!!!你的眼里只有他,但他的眼里不是只有你,或者,他的眼里根本就没有你——世界上最痛苦的事莫过如此。
白晓丽的脑海里一边意识流般浮现着以上的想法,一边手里也没闲着,她赌气似地把东西往包里死命地塞,直到塞不下为止,甚至那些个不需要的东西也被她莫名其妙地按到包里:企鹅小闹钟、嘟着嘴的小猪茶杯、文具包、名片夹……叮叮咣咣噼里啪啦一阵乱响,引得坐在附近几个同事纷纷引头观望,看到白晓丽这幅神经质的模样,又不好问,只能坐下去在格子间后面窃窃私语:“伊要做啥?”“是不是失恋了?”“哦哟,搞不好被人骗色骗财!”。
白晓丽搞出那些动静就是想引起李万翔的注意,哪怕他走出办公室问一声怎么回事,自己也会找个台阶下,随便说个“头疼肚子疼”的理由请半天假,可他没有。白晓丽越想越气,忍不住拎起包冲出格子间,连假也没请就回家了。心里恨恨地想:我倒要看看你李万翔的公司离了我还怎么转?
李万翔轻轻地,无声地咧了咧嘴,他好像听到了白晓丽心中的碎碎念叨,刚才那些动静,李万翔都听到了,但他依旧保持自己的一贯作风,稳若泰山摧之弥坚,不闻不问由她去,听到“嘟嘟嘟”的声音,那是皮鞋跟踩在地板上的回声,渐行渐远。他知道,白晓丽走了,他还知道,白晓丽肯定会回来的。
他不会追出去,因为眼下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等待和处理。
白晓丽走后,李万翔就坐在办公室里,如老僧入定般纹丝不动。不知过了多久,办公室门口传来了“笃笃”的敲门声,轻轻的两声响,不轻不重,没有脚步声,没有咳嗽声,李万翔知道,是徐林生来了。
进。一个“请”字也免掉了,说明这两人的关系要么极为糟糕,要么极为亲近。
个子瘦高的徐林生轻手轻脚地走进来,墨黑羊绒衫,藏青长裤,不起眼的眉眼掩藏在寡淡的一张脸上,极少开口说话的他,常常让人忘了这个人的存在。
徐林生走到他的办公桌前,正欲开口,李万翔说,“只说结果。”
徐林生点点头,“办妥了。”三个字,一口气,李万翔却像嘘出了三座大山,他点点头,轻轻地“嗯”了一声,徐林生退出了办公室。
李万翔还是端坐在老板椅上,表面看上去如一湾春水波澜不惊,但其实内心的小宇宙都要爆发了。一瞬间,他想了很多很多,想回家和老婆说说笑话,想亲亲儿子的红脸蛋,还想对白晓丽诚恳地说声“对不起”。不着急,还有时间,慢慢来。李万翔几乎是跳跃着起来,收拾收拾,准备拎包回家。
极度绷紧的神经几天来终于有一丝丝放松,随即一丝倦意席卷而来,一点点的,酸泠泠的感觉像蚂蚁一样顺着大腿细细密密地爬上来。李万翔罕见地打了个打呵欠,机械地把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往包里面塞:gucci钱包、度身定制的vertu手机,包金的parker钢笔,hermes笔记本…。
若是平日,李万翔会有一种细细品味的闲情,面前摆放的这些流光溢彩精雕细琢的用品,动辄上千上万,仿佛是他的战利品:和女人一样,男人对于上乘的奢侈品,也会有一种欲罢不能沉溺其中见之就要拥入怀中的病态心理。尤其是认识周娜以来,中年男人讨好小女生、处处要显阔露富的心态加上人到中年重拾爱情的浓情蜜意、初见伊人爱恋炽热的情感,让李万翔在过去两年中带着周娜,近乎疯狂地到全世界各地购物、旅游、拍照留影。那时候的周娜,眉眼间的妩媚与风情,笑起来时嘴角的梨涡,配上她最爱穿的白衫迎风飘遥——仿佛已是一幅雕塑,永久地镌刻在李万翔的脑海中。那时候的周娜仿佛杨柳青青,依人而立,娇俏可人。
“可惜啊,人不能两次跨入同一条河流,过去的再也回不来。”李万翔自嘲地摇摇头,扫视了一遍桌面,准备拉起拉链,锁上抽屉,走人。
就在一瞬间间,“周娜”这个名字像着了魔似的要钻入李万翔的脑海里,心房里。“周娜?!周娜是谁?”李万翔歪着脑袋,似乎在回忆一件很久远的事情,慢慢地,前尘往事渐上心头,昔我往矣,唯见杨柳依依,今我来思,恰逢雨雪霏霏。
回首望见窗外,果真又飘起了小雪花。李万翔想到了什么,神经质地拉开已经关上的提包,把包里的东西一股脑儿的倒出来,摸索着在皮包的夹缝里寻觅,却是空空如也。李万翔停不住似的加快速度,打开hermes笔记本,翻看着里面有没有夹着纸条,还是没有,他听见自己的心突然间敲鼓般“咚咚”直响,手也抑制不住地抖起来,“究竟放哪里啦?”
抽屉里没有,钱包里也没有,口袋里更没有,目之所及,手之所至,依旧没有。李万翔觉得腿有些发软,险些一屁股坐到地上。这时耳边听着办公室外的一阵阵喧哗声,手上脚上却使不上劲,仿佛夜梦中被魇住了一样:分明是醒着的,却怎么也动弹不得,胸口被异样的怪物压得死死,几乎要窒息了,意识如此清晰,可是不能呼喊,不能逃走,只能眼睁睁地等着恐怖之神一步一步走近……
就在李万翔陷入梦魇一般的恐惧之中时,办公室的门被猛地推开,平时李万翔就没有反锁的习惯,因为白晓丽永远会在那里替他挡住一切不速之客。
可今天,白晓丽不在,就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是周娜——野心勃勃地要艳压牡丹,天下来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