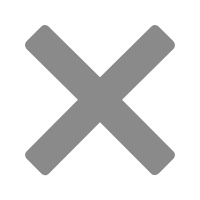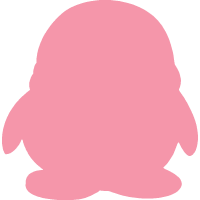第 2 章节
静。
小芳和其他售楼人员已经吓得躲在一旁,动也不敢动。眼见李万翔进来,都像捞救命稻草般蜂拥而至身旁“李总,李总”不迭地喊着。销售经理李如松是李万翔的堂弟,看到这副情形,急忙向李万翔使眼色,示意他不要暴露身份,马上离开,因为一旦惹上这些人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李万翔只是迟疑一会,身边就已经围满了人。为首的正是吴晓仁,他用青筋爆出的左手钳住李万翔的右臂,琥珀色的眼珠子瞪得溜圆,一开口嘴里冒出一股腥味,不知是吃了大蒜还是肠胃不好:“你就是高翔公司的老板吧?我爸爸死在你们楼盘了,凶手肯定是你们公司的人, 你们总要给个说法吧!”话音刚落,周围的人一阵嗡嗡“是啊”,“就是”,“反正不能让他跑了”,李万翔也没听清说些什么,只觉得唾沫星子溅了一脸。
就在这一刻,李万翔反而冷静下来,先前的忐忑不安瞬间落入尘土:一切都会有个了结,峰到最高不觉险,李万翔听到自己心底一声轻笑。他轻轻地,然而是有力地摆脱吴晓仁的左手,威严地扫视了四周,动作幅度不大但蕴含之意不言而喻,周围的人见状顿时安静下来,十几双眼睛盯着他,活像暗夜里的猫眼,碧绿发光,就等李万翔出什么妖招。
静了几秒,李万翔开口了:“各位叔叔阿姨,阿哥阿姐,我是高翔公司的总经理李万翔。你们的亲人吴德仁先生发生这样的事,我比你们更痛心。为什么呢?一,是因为吴先生是我们的客户,客户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吴先生来我们楼盘看房购房,是给我们生意做。各位想,于情,我和我们工作人员是希望他健康长寿,还是希望他遭此横祸?二,我公司旗下销售的楼盘发生这样的不幸,势必影响后期销售进度,于理,我们公司更不希望吴先生遇到不测。!所以,”李万翔停顿下来,环视四周,“我以我的人格向各位担保,吴先生绝不是他杀而死!”
吴德仁的老婆、亲戚都不吭声了,一会他的儿子憋出一句:“那你们这么大的公司总得给我们死者家属一个交代吧!”说完舔舔嘴唇,许是哭得太久,口干舌燥。
李万翔见了,连忙对李如松说:“还不赶紧给各位家属泡点菊花茶?大家还没吃午饭吧?我请各位到‘阿婆红烧肉’吃个便饭,我们边吃边聊,”说着,亲自递给吴德仁老婆和儿子各一杯菊花茶,又拍拍吴晓仁的肩膀:“走吧,人是铁饭是钢,边吃边谈不误事。”
接下来一个小时,李万翔和吴晓仁单独在一个包间里不知谈了些什么。走出包间时,两人神色无比轻松自如,尤其是吴晓仁仿佛卸下重负一般,忍不住要笑出来,又拼命把笑意忍回去。李万翔看在眼里,心知这场闹剧快结束了,主角都不演了,看客们便会无趣地各自散去。
回到售楼处,正碰到在现场调查的派出所警官——朱警官和邹警官。他们一见到李万翔就伸出手来想握手攀谈,李万翔一边握手,一边扭头看吴晓仁,示意他说话。果然,吴晓仁咧着大嘴说:“警官,我们和李总这边调解好了,之前有点误会,现在我们家属要求撤诉,我准备把我爸火化!”说话间一股酒气自口鼻传出,弥漫在售楼处。
两位警官心下好笑:早上还要死要活,一定要我们查出真相,揪出凶手,这么快就变了,钱真是个好东西。
年岁稍长的朱警官说:“何时结案并不是由家属决定的,而是我们警方根据调查结果决定的。请家属放心,我们决不会冤枉一个人,也不会错放一个人的。”
吴晓仁一听急了,“啊?还要查,我们家属都相信是失足落下电梯间的,你们还查个毛啊?”
邹警官说:“抱歉吴先生,警方这也是例行公务,哪怕明知不是自杀和他杀,我们也必须拿出调查结果,才能结案。”
吴晓仁像个瘪了的气球,垂着脑袋不敢看李万翔。原来他俩刚才已经达成协议:只要家属不追究,李万翔公司便会赔偿五十万给他个人,连他母亲都没份。吴晓仁想,要是闹到法庭上,不一定能赔这么多,还要请律师,说不定要跟母亲平分。不如干脆私下调解,神不知鬼不觉拿到钱,这才是大爷。所以他很爽快地答应李万翔的条件,可没想到,警方还要继续查下去,也不知李万翔会不会藉此食言,吴晓仁有点不知所措。
李万翔清清嗓子,说了太多话他已经近乎疲劳崩溃:“没关系,清者自清,查到最后肯定还是失足致死。那吴先生,我们就等警方调查结果出来再履行赔偿协议吧!”吴晓仁只得点点头,先行离去了。
“李总,能借一步说话吗?我们有几个例行问题要问。”朱警官说。
李万翔从心底冒出一句国骂,脸上却挂着一丝微笑:“当然可以,去我办公室吧。”
邹警官问:“据我们调查得知,A座所有楼道的电灯已经安装好,为什么今天上午楼道里却没有一盏灯能亮呢?”
“因为今天上午施工方停电停水检修线路。”
“你们售楼处事先知道吗?”
“施工方会提前一天通知我们。”
朱警官接着问:“你们售楼处几点上班?”
“九点。”
“为什么吴德仁今天八点就来看房呢?”
“这就要问吴先生本人啦,据我们售楼处人员说是吴先生自己要求提前一个小时看房,因为要早点赶回厂里上班。”
“事发时,你们公司售楼人员在干什么?”
“据我们售楼人员回忆,她和吴先生当时正在A座501,小芳刚好接到一个电话,吴先生就自己走到门外,因为楼道漆黑,他没有看清楚电梯间的情况,就走进去了。那个单元的电梯刚好没安装轿厢,所以吴先生遭此不幸。”言未尽,李万翔的眼圈都红了,“我会和开发商沟通,给死者家属满意的赔偿金。”
至此,警官认为不需要继续调查,于是他们告辞离开。
李万翔踱进洗手间,用冷水拼命浇脸,过了好久,才抬起头看着镜中那张湿漉漉的脸,恍然间变得不再是自己,心中一个激灵,冷汗直出。花瓶里的那支康乃馨几天没有更换,那红色不再是鲜艳欲滴,而是乌墨墨,粘乎乎,看起来像死者的鲜血,让人反胃。李万翔想起来,从早上到现在,他已经十个小时不吃不喝了,“是该结束了,”他想。
下午四点,迎着黄昏的斜阳,李万翔独自一人驱车返回公司。路上特意绕了个圈去了朝曦路,那里,有他和周娜的爱巢。他不用抬头望去,就能想像身后林立的窗中,有一扇窗后就立着他的心上人,遗世独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俩从当初的爱火缠绵到如今的渐行渐远,李万翔没有踩刹车,直接以八十码的速度驶过,只几秒钟X6就剩下一个小黑点。
只不过有一点李万翔错了,今天周娜并不在窗后,李万翔甫一离开,周娜的红色马自达就驶进朝曦路,她刚刚见过李万翔的太太——林秀娟回来。两人就这样擦肩而过,仅仅是隔了几秒钟,却是咫尺天涯。在对的时空里,遇见错的人,也许注定了他们的命运就像两条命题错误的平行线,曾有交集,却终将延伸到不同的空间里。
五、疑云乍起,风波未平
一坐上警车,邹辉就做闭目沉思状,这和他平时咋咋呼呼的大嗓门形象相距甚远,朱甘强有些好奇,但想到也许年轻人昨天熬夜看足球赛,今天又查了一天案,真的有些疲倦了,想到这,他也闭目养神起来。
四点多,他们回到了派出所。邹辉仍然默不做声,闷闷不乐的样子,朱甘强忍不住笑起来,拍拍他的肩,说:“怎么了,小邹,是不是你的AC米兰输球了?”
邹辉轻轻一笑,说:“老朱,你怎么看这个案子?”
“还怎么看,失足落下五楼摔伤致死。”
“可我倒发现有几个疑点。”
“哦?!说来听听。”
“第一,吴德仁只是江南工厂的油漆工,年收入不过两万八。听同事介绍,他还爱赌博,老婆常为这件事跟他争吵。他的老婆不过在巷口摆摊做做早点,据调查一年收入最多不过两万。至于他的儿子,至今还在领失业保险。这样的家庭,存款不超过五万块。你说,吴德仁怎么会有能力买得起‘在水一方’的房子?要知道,那里的房子最便宜的一套也要八百多万。今天早上他看的这套A座501可是市价一千万。这钱就是吴德仁一家三口不吃不喝存上一百年也攒不够啊!”
“嗯,有点意思。”
“第二,刚才我询问李万翔,他说今天是施工方停电停水检修的。”
“对啊,这有问题吗?”
“可我又问他,他们售楼处知道吗。他说施工方会提前一天通知他们。”
“嗯,说下去。”
“也就是说,在吴德仁要求看房之前,他李万翔和高翔公司售楼处都知道A座今天要停电停水,既然知道,为什么偏要带客户到一片漆黑的单元去看房呢?”
“小芳不是说带了个手电筒吗?”
“可这不符合常理啊!通常这种情况,她们完全可以给客户解释说今天停电,改天再看,或者先看其他房型。为什么一定要冒险呢?”
轮到朱甘强默不做声了。
“第三,李小芳说吴德仁走出房间时,她正在接电话,你问她是什么电话,她说是一个打错的电话。我让小叶去电信局调出李小芳今天早上八点到九点的通话记录,期间只有一个来电,八点十八分,是一个手机号码,查不出机主身份证号。可有一点很奇怪。”
“什么?”
“李小芳说是打错的电话,可通话记录显示,这个来电的通话时间是八分钟。八点十八分打进,八点二十六分才结束。一个打错的电话,能让机主通话八分钟?而且正是这八分钟里,吴德仁走出房间,因为看不清电梯间的情况,才一脚踏空掉下去。试想,如果像常人那样,得知对方打错了,立马挂断,至多五秒,完全来得及追上吴德仁,阻止悲剧发生。”
朱甘强点上一支烟,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还有最后一点,在死者摔死的现场,我看到死者的手提包是落在死者的背部。这一点也让我非常疑惑,一般说来,死者落下时,要么是惊恐,先把手提包松开,那手提包会落在尸体的下方;要么是死死攥在手中,那么落下时手提包应该跟尸体同一个水平面。怎么会包后于死者落下呢?”
听完邹辉的一段话,朱甘强连忙站起,按灭了尚在燃烧的香烟,揉揉太阳穴,笑说:“小邹不错,有点见识。不过我们办案还要冷静,今天也累了,先回去再考虑考虑,也许会有新的发现。”
邹辉一听,自己也真的累了,前段时间一直忙于刑事案侦破,昨天又熬夜看球赛,今天整整一天都没歇会。难得这会没有其他事能按时下班。于是点点头,两人告别。
当林秀娟听到一阵急促的“噔噔”上楼声,她意识到已经下午四点,阿姨已经接儿子放学到家了。她连忙坐起,扯过床头的面巾纸匆匆擦了把眼泪,还来不及去洗手间梳理一下头发,洗洗脸,儿子李高梓已经一阵风似的冲了进来,口里还高喊着:“妈妈!”林秀娟忙上前一步,迎着自己的心肝宝贝,看着快到自己下巴的儿子,红通通的脸蛋像个苹果,她紧紧地搂着他,生怕他会飞走一样。
李高阳觉得有些奇怪,抬起眼看着妈妈:“妈妈,你怎么啦?”
林秀娟摇头,又笑着点点头,“妈妈没事,就是有点头晕,现在已经好了。快去吃个苹果,做作业吧,妈妈晚上给你烧大虾吃。”
几乎就在开口的这一刻,林秀娟下定了决心——忍,那是将刀架在自己心上慢慢磨啊!多少不能说尽的辛酸与苦楚,可回头一想,自己的年龄和背景早已经不起任何折腾。她就不相信,自己和李万翔十二年的夫妻,还敌不过这半路小三?怯弱无能如林秀娟,竟然也鼓起勇气暗暗告诉自己:等万翔回家,找他好好谈谈。无论以前发生任何事,我和儿子都会原谅他,希望他回心转意,我们一家人重新开始。
人的痛苦其实来源于思想的痛苦。思想一通,林秀娟突然间像打了鸡血般高亢起来,安排儿子做作业,同时三下五去二把房间收拾妥当,虽然白天阿姨已经打扫整洁,但她忍不住神经质地拾掇拾掇。现在最难的事情来了:给林秀娟自己收拾。
一看到镜中的那张脸,林秀娟刚刚的兴奋劲又逃到九霄云外。那张发黄的,略有些浮肿的脸,突出的眼泡,怎么梳理也是毛毛燥燥的短发乱飞,若隐若现的褐斑,连自己看了都提不起兴趣,难怪自己的男人会移情别恋。一想到这里,林秀娟的心就像刀割般难受。
“明天开始,不,就今天晚上开始,我要练瑜珈,长跑,喝瘦身汤,做美容,读书,……”林秀娟有些神经质地喃喃自语,“我要让万翔看到全新的我。”
六点钟,李万翔带着曹月丹打开门进来,看到林秀娟正在餐厅摆餐具,一切一如从前,又有些变化,具体什么变化,李万翔又说不上来。等林秀娟一开口,他就知道变化在哪里,——这家的女主人变了。
只见林秀娟将从前披散的烫发高高束起,盘在脑后,前额处还用一枚亮钻蓝发卡别住;往日姜黄的脸色今天腻白腻白,应该是多涂了两层粉,嘴唇上殷红一片,有一些唇膏还粘到牙齿上,开口说话时,一开一合,特别扎眼;往日从来不开的中央空调今天也破例调至高温,整个房间温暖如春,林秀娟穿上一件从未穿过的薄毛衣,黑色带亮片,胸前的图案花里胡哨看不出名堂,腿上是一条黑色打底裤。整个打扮倒是比平时洋派许多,但这个衣服却把她的身材弱点暴露无遗:下垂的胸,凸出的小腹,粗胖的大象腿。
李万翔呆呆地看了一会林秀娟,心想:这是唱哪门子戏,丑人多作怪。林秀娟看他痴痴地看着自己,连说什么都没听进去,心里不由得暗暗窃喜:看来改变形象有点作用了,以前万翔从不这么看我。
正要开口,李万翔说:“二姐的女儿也来了,她要在我们家住段时间。月丹,这是舅妈。”林秀娟这才看到,李万翔身后还站着个人,顶着一头金黄的烫发活像金毛狮王,夸张的耳环,上身是一件金黄色的短小夹克,配上里面的豹纹打底衫,下穿一条破洞牛仔裤,脚踩松糕鞋,活像街头小太妹。
林秀娟暗暗不喜,但也不好说什么,只好点头:“来了,先吃饭吧!”
白色橡木的餐桌上已经摆上四菜一汤:油焖大虾,山药烧排骨,蒜泥菠菜,雪菜炒毛豆,汤是鲫鱼豆腐汤。虽是家常菜,却是大厨手艺:红黄白绿,荤素搭配,色香味俱全。饿了一天的李万翔看到这些菜,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洗换完毕就一屁股坐下来大口吃饭。
柔和温黄的灯光配上餐盘上袅袅升起的热气,房间里的气氛氤氲而温馨,李万翔一边大口吃饭,一边问问儿子学习情况,讲讲老师和同学的趣事;林秀娟坐在对面,看着眼前的情景,忍不住泪眼模糊,想:有多久没有这么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啦!要是永远这样我就别无所求了,自己已是个失业的中年妇女,只要老公能回头,还计较什么呢?
正在遐想时,忽然看见李万翔对着她说话,林秀娟连忙把思绪收回来,假装揉揉眼把眼泪抹去,一句话飘进耳里:“二姐现在的依靠只有月丹,现在她住在我们家找工作,你要帮我们照顾好她,要把她当自己女儿一样看待。”
林秀娟唯唯点头,除此之外她能说什么呢?她能说,“你们家来个人住在我家,有跟我商量过吗?这个家是你一个人的吗?”或者说,“你二姐自己亲生的女儿都管教不住,十几岁的大姑娘扔给非亲非故的我来管,出了什么事,谁来负责?”不,这些她都不能说,别说现在的林秀娟希望藉此机会挽回和李万翔的关系,没有这事之前,家里的事也是李万翔说了算,林秀娟只有听从的份。她不是圣人,心里有不快又不能发泄,自然脸色就阴沉下来。
曹月丹在一旁听了,心里默默发笑,人小鬼大的她一直担心舅舅看她贸然前来会大发雷霆,甚至会给她买张返程票把她送回去;又担心舅妈是个强悍的女人,给她颜色瞧,现在看来,舅舅还是心疼她是自家孩子,而且还答应给她找工作,舅妈嘛,不过就是个家庭妇女,家里的事她说不上话,看来自己这次来魔都是来对了。
李万翔看着林秀娟那呆滞的神情,用筷子夹菜又放下,欲言又止的模样,滑稽搞笑的妆容和服饰,不知怎地一股无名之火升起。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李万翔觉得林秀娟怎么做都是错:对他百依百顺,他觉得她畏畏怯怯,缩头缩脑,不像阔太太,倒像是保姆阿姨之类;一旦不听从他的意见,或者表现出不满的情绪,他又觉得“老子在外这么辛苦养家,你们都是靠我才能有今天,居然敢违抗我的意见!”边想边吃,再好的美味也食之无味,如同嚼蜡了。
李高梓看着餐桌上的三个人,神态各异,各怀心事,妈妈又露出惯常失落幽怨的神色,爸爸则是眼皮也不抬,拼命往嘴里塞东西,气不打一处的样子,对面的表姐则不时摆动她的耳环,筷子在盘子里飞快游走。才十一岁的他早就学会看大人脸色,心知这表面宁静安详的现实,恰恰背后掩藏了波涛汹涌诡谲莫测的未来。
六、青山依旧在,故人难再返
邹辉先行离开办公室,朱甘强才吐了口气,放松地点燃第二支烟。一个个烟圈吐出来,飞走,又继续吐,狭小的房间里一片烟雾迷蒙,这时的他才敢真正地面对自己内心。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邹辉在场,或者参与调查案件,朱甘强就越来越不自在。看到他在调查现场犀利的提问,对那些自己从未注意到的细节穷追不舍,在领导和同事面前侃侃而谈对案件的看法,朱甘强就如坐针毡。
说起来原因很简单:他比邹辉大了近一轮,邹辉进警局还是朱甘强带着他实习,起初几年邹辉还尊称他“朱老师”;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改口叫他“老朱”;这还是客气的,碰到朱甘强对他的看法有不同意见时,邹辉往往得理不饶人,年轻人开玩笑有时难免过火。
比如汶川大地震时,有一头猪名唤猪刚强,名字正与朱甘强一字之差。自从邹辉知道这个新闻,只要朱甘强跟他争论几句案情,彼此说服不了对方,邹辉就半开玩笑半带讥讽地拍拍朱甘强的肩,说:“哎,我说老朱啊,你和猪刚强真有一拼,这么明显的案情,明明是我对,你还硬要跟我抬杠。”弄得朱甘强哭笑不得,生气,人家会笑话他气量太小;忍了,邹辉会得寸进尺。怪就怪自己不争气,在警局混了这么多年居然还只是个普通科员,经手的案子没有一桩是自己独立破案,更别提有立功表现了。眼看着奔五十的人了,再混几年就要退了。
再看邹辉这小子,春风得意,来刑侦科几年时间已经破了好几起大案,颇受上级青睐,解决级别问题指日可待。要知道他才三十来岁,这辈子混个处级都未尝不可能。可邹辉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恃才傲物,一副舍我其谁的模样。遇到更厉害的对手,他也会心悦诚服地低下头;可遇到类似朱甘强之流,他往往话里带刺,只差不明说“你是庸才,不配与我争论”。
后来,朱甘强就真的不再与他争论,都是迎合附和的态度,即使邹辉话中带刺,朱甘强也一笑了之。虽然心里愤愤,但他还是给足邹辉面子,就这样两人磕磕碰碰在一起合作了几年。
朱甘强心中早就不甘屈于邹辉之下,但又不知从哪里着手可以让自己翻身。他一边无意识地翻着案卷,突然眼前一亮,机会来了,—一个熟悉却又久违的名字映入眼帘:徐林生,身份是高翔公司总经理专职司机。今天上午他接受了朱甘强同事的问讯,为李万翔今晨七点至九点的行踪作证。
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个徐林生是朱甘强的远房亲戚,两个人还同在一个部队里当过兵,一起复员到地方。朱甘强因为家里有点门路就进了警局,徐林生家境贫寒,除了会开车又没有其他特长,只好应聘到公司当司机。两人多年未联系,“但现在,我们该见见面了”,朱甘强边想,边轻轻合上案卷。青黑的烟霭把他的脸掩盖起来,看不出那张脸上的丝毫表情,只知道朱甘强掏出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手机屏幕的幽幽蓝光在暮色渐沉的办公室里忽明忽暗,让人的心情也起伏不定。
李万翔闷头扒了一大碗米饭,只觉得心口堵得发慌,连忙站起来往洗手间冲去,一阵干呕之后,又觉得肚子往下坠,赶紧坐到马桶上,做蹙眉沉思状。他有便秘,但今天其实不是便秘引起的,而是饿了整整二十四小时的胃吃不消它的主人在短短半个小时内装下的那许多美味:虾、排骨、鱼、米饭……,它要罢工了,给这个脑子搭错了的主人一个小小警告。
李万翔何尝不想正常进餐,他本是就是个美食家,美味当前食指大动,何等大快朵颐!可从昨晚开始他就没心情吃饭。他告诉林秀娟要去外地接一个客户,其实是接到了周娜的一个电话,说是有性命攸关的事情面谈,于是李万翔快马加鞭地驱车前往两人在朝曦路的公寓。
一推开门,就看到周娜蓬头散发地斜躺在客厅的白色真皮沙发上,未施粉黛,尖尖的小脸反而更显清丽,只是身穿一件普通的白衬衣配上浅蓝的微喇牛仔裤,居然还是赤脚!
看到李万翔进来,周娜起身踏在地毯上,往前几步,伸开双臂做欲拥抱之势,李万翔只看到一个风摆杨柳般的婀娜身姿扑入怀中,他紧紧搂住对方,把脸深深埋进那一头乌黑的长发中,贪婪地嗅吸着对方身上散发出的那股清甜别样的香味。
李万翔还闭眼沉醉在这份香味之中,耳边传来了一阵娇柔的泣声伴着些喘息:“万翔,我,我……”他连忙睁开眼,把怀中人儿的小脸扳过来,急急地问道:“娜娜,怎么了?”
周娜脸上泪湿满面,黏上几根长发,往日丰盈水润的嘴唇都有些干裂,翘起几块角质,看样子有段时间没吃没喝了。李万翔见状更加心疼,用手轻拍周娜的背部,触摸到两块突起的肩胛骨,忍不住追问:“宝贝,怎么啦?”
周娜轻轻回转身,示意李万翔看茶几上,李万翔半天摸不着头脑,弯下腰仔细寻找了一会,才在一堆白色餐巾纸中发现一张狭长的纸条。他拿起一看,耳边居然有种“嗡嗡”作响的感觉:白色的试纸显示有两道清晰的红杠杠,活像中队长队牌。难道这就是民间笑称的“恭喜你,荣升中队长”?李万翔觉得这个玩笑开大了。
他扭过头,看见周娜还站在一边,闭眼,无声的哭泣,微红的鼻翼翕动。他搂过周娜的肩膀,把她轻轻地按到沙发上坐下,帮她掠顺长发,扯过餐巾纸把她的小脸蛋揩拭清爽,又起身倒了两杯水放在茶几上,示意周娜喝掉。这才缓缓地开口:“娜娜,我们不是一直用避孕套的吗?这个试纸会不会不准确?”
“什么?”周娜猛地抬头,差点碰掉李万翔手中的杯子,“你觉得我有必要编这么个谎言骗你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算了,没什么意思。”停了一会,李万翔又说,“娜娜,我有个建议,”他斜眼看了看周娜的脸,见她面无表情地端坐着,忍不住要哄哄这个比自己小二十岁的姑娘,“毕竟还是个孩子嘛!”李万翔告诫自己要冷静。“我是想说,要不我们去医院复查一下,然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万翔,——”周娜一头埋进李万翔的怀中,边哭边说:“我,我不想去医院。你想,我一个二十一岁的黄花闺女去医院做孕检,算怎么回事?同学老师怎么看我,我怎么跟爸妈交代?”李万翔只见到周娜的双肩不停耸动,感觉泪水鼻涕糊了自己一身,尽管如此,可美人的哭也是那样风情万种,让人千回百转,牵肠挂肚。
李万翔到底是男人,再困难的事情也要硬着头皮解决,他用手轻轻抚摸着周娜的双肩,低低地说,“宝贝,别哭了,哭多了可要生皱纹的。”哭泣声果然频率慢下来,李万翔见状,又接着说,“要不我们先吃饭?边吃边聊?”
周娜抬起头,李万翔这才看见她的眼睛都哭红了,忍不住心疼地吻了吻她的明眸,私心里也希望凭借这样的举动,唤醒从前的周娜:像只小猫咪,偶尔闹闹无伤大雅的小脾气,用爪子挠一挠,但不会真刀实枪;只要男人哄一哄,其他时间还是温柔体贴,驯服听话,甚至有时候让人觉得傻的可爱。女人嘛,还是头脑简单得好。
但这一次,周娜可就不买账了,她擦干眼泪,正襟危坐,然后摇摇头,板着脸说:“我不吃饭。”
李万翔都有些冒火了,“那你要怎么样?”
“我要你给我个说法。”
“说法?什么说法?”
“万翔”,看到李万翔不似往日般低声下气,周娜的声音就软下来,开始发嗲,“我十九岁就跟了你,你是我的第一个男人,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人家心里害怕嘛!”
“我知道你害怕,我这不是马上就赶过来陪着你吗?”
“可是,现在,我怎么办呢?拖下去总不是办法。”
李万翔愣住了,是啊,怎么办呢?拖下去总归不是办法。他微笑起来,“娜娜,你心里怎么想呢?”他觉得以自己对周娜的个性把握:爱美,保持苗条,贪玩,喜欢购物。九○后的典型:自己还是个孩子,怎么会在二十出头年纪就养小孩呢?
但这次李万翔好像失算了,周娜一字一句地说:“我、要、把、这、个、小、孩、生、下、来。”
李万翔头都大了,他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事都失去控制,都不听自己使唤,过去四十年中那种宁静、平逸、顺水顺风的日子为什么就再也找不回;他不明白女人为什么总想用生孩子拴住男人,上至四十岁的阿姨,下至未满二十岁的小女生;他不明白为什么女人到最后总是那样蛮不讲理,那样固执任性,感情用事?
但他是男人,这个时候不能意气用事。他轻轻摇晃着周娜的肩膀,硬是挤出点笑容:“宝贝,这个问题我们等会再聊好不好?我知道红河路上有一家新开的泰国餐厅,很有情调的,我带你去尝尝……”
“不,不,”周娜今天像是打了强心剂,铁石心肠般,斩钉截铁地说:“今天你要是不同意我的想法,我就绝食!”
“娜娜,你这是不是有点无理取闹?生下来?!说得轻松,生下来以后怎么办?你想过吗?你的学业怎么办?孩子是非婚生子,你让他以后怎么在社会上抬起头?”
周娜仿佛知道李万翔会提出这些问题似的,她倒笑起来,嘴角边梨渦娇俏,仿佛醇酒荡漾,让人不饮自醉,特别像许晴。两年前,李万翔就是被她这样的笑容迷得神魂颠倒。
“老公,这件事其实很简单。”
“?”李万翔拿眼看着周娜,表示疑惑。彼时心中已有答案,只待对方说出来。
“把你们家的那个黄脸婆赶出去,我们俩结婚。”后半句是温和的,笑盈盈的,然而是杀气腾腾的。
虽然李万翔的爱情世界里早已摒弃了这个与他共度十二年婚姻的女性,——林秀娟。她于他,仅仅只是那些饥肠辘辘时适时摆上的饕餮美味,或是儿子口中的“妈妈”,还是老人眼中正宗的儿媳。而他,早就记不太清林秀娟的五官轮廓,她就像那套复式房里移动的家具,他对她的熟悉度还远不如自己的那本IPAD来得熟稔。而今天,此时此刻,林秀娟的模样却清晰地浮现在李万翔眼前。
李万翔和周娜从来都没谈及林秀娟这个名字,从来都是以“她”来指代,今天自周娜嘴里冒出这个“黄脸婆”的字样,听在李万翔耳朵里,确实尤其刺耳。因为这也无形中贬低了李万翔的审美观、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