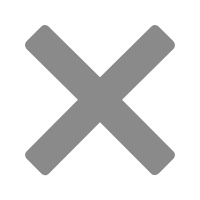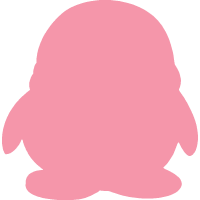-
前妻重生记
本书由中意小说网进行电子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 1 章节
一、东邻有女,倾国倾城
有人说,这世上有两种女人:一种女人是蚌,拼尽毕身心血,呵护一粒外来的砂子,最终用灵与肉将这粒砂子育成一颗珍珠;另一种女人是鹬,平日悠闲乐哉,好不逍遥,借机四处觊觎别人家的宝贝。一旦发现珍珠,便不由分说使出浑身解数抢将过来,成日挂在嘴上,专以自诩。
不过,眼下林秀娟可没心思想这些个闲极无聊的话题,自己究竟属于哪一类女人。想想就肉麻,自己就是女人,一个普通女人而已,说什么蚌啊,鹬啊,想这个问题,不如想想晚饭做什么来得实际。
眼看着客厅的钟摆指向下午三点,秀娟便准时换上那件灰外套,摆在门口的敞口黑皮鞋,她看也不看就准确无误地将脚塞进去。这一切就像设定好的程序,只需按时启动。只是今天秀娟穿了一双白色棉袜,衬得黑色皮鞋格外刺眼。放在十年前,她会毫不犹豫地换上一双黑色或者肉色丝袜,可十年后的她连想都没想就径直出了门,有谁会在乎一个十岁孩子妈妈的穿着打扮呢?一切都那样波澜不惊,平淡无奇,自己早过了对镜贴花黄的豆蔻年华。一想到自己居住的魔都,可谓是国际性大都市,可不照样有阿姨爷叔之类,穿着睡衣上街买菜、遛狗、逛超市……秀娟心下立即释然,还忍不住浮出一丝笑容。
就这么走出家门,路过小区门房间,林秀娟很有礼貌地向小区保安点点头,保安还以点头致意:“林阿姨,出去啊!”秀娟也不答,从小区移门的反光镜里,她看到自己的模样:蓬松的烫发,深冬的风吹得凌乱不堪,活像个鸟巢。灰色直腰的对襟羊角扣外套,洗得发白的牛仔裤,黑皮鞋,白棉袜,身高一百六十公分,体重六十五公斤,年龄三十六岁,脸色微微发黄,额头隐隐若现几条皱纹,嘴角下垂,法令纹明显……
林秀娟是这座人口两千万的大都市中最平凡不过的一个路人,套句网络用语:我是来打酱油的。可秀娟觉得,自己有时候连打酱油的都算不上。那打酱油的起码还有热闹看,可她自己已经多少年没有看过热闹了。但她不知道,马上,不到十分钟之内,就有一场人生中最大的热闹降临到她身上,而且,她是主角,只不过,是被主角而已。
出门直走,两百米右手转弯,再走十五分钟就有一家净菜市场。这条路林秀娟闭着眼都能走到,她原打算享受着悠闲的午后时光,买几个好菜,晚上做顿丰盛的晚餐,犒劳一下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被她称为“吉祥二宝”的——儿子和老公。
可今天林秀娟是注定走不到她的目的地了。一个身影拦住了她的去路,林秀娟猛地一惊,骤然抬头,才看清对面不知什么时候站着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年轻女人,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比自己高出一个头左右,至少一百七十公分;看上去至多二十岁出头,青春无敌的脸庞光洁无瑕,忽闪的大眼睛,微微撅起的嘴唇,厚而性感;只扎着一条马尾辫,却是风情无限,已是冬寒时节,这女人,不,这女孩穿着开衫,短裙,丝袜,配高筒皮靴。站在这样一个光彩逼人的女孩面前,同为女性,林秀娟觉得自己寒碜极了,心里直懊悔为什么不化化妆,换套衣服再出门。两厢对照,她还没开口,气势上就矮了一大截呢!
还没来得及容林秀娟胡思乱想完,这女孩开口了,淡粉的唇彩在冬日阳光下一闪一闪,林秀娟真心觉得对方好美,耳边却飘来这么一句话:
“你就是林秀娟吧?” 林秀娟愕然,她一直以为女孩是问路的,或是认错了人。
还没等林秀娟回答,这女孩大概看到她呆滞木讷的神情,微微一笑,忍不住的傲然于色,继续说:
“你老公就是李万翔啰!?万翔没有跟你说过我是谁吗?”
林秀娟只觉得血往头上涌,眼前一阵阵发黑,喉咙发干,她嗫嚅着干裂的嘴唇问:“你……你是谁?”
女孩轻蔑一笑,既有些胜券在握,又有点厌恶鄙夷地说:“我叫周娜,回去问问你老公就明白啦!”说完扭头就走,林秀娟还记得她远去的背影:屁股一扭一扭,活像模特在走猫步,高筒皮靴踩在水泥地上“嗵嗵”直响,仿佛踩着林秀娟的心,生痛生痛。只见这女孩掏出一串钥匙,上了一辆红色敞篷车,倏忽之间绝尘而去。
林秀娟至少在原地站了五分钟,还在发呆。如果不是引起周围一些路人的频频回首,她会一屁股坐到地上,嚎啕大哭一场。可现在她担心这四周打酱油的人中有不少熟识者,于是秀娟只好拖起老气横秋的黑皮鞋,迈开如千斤重的步子慢慢走回家里。
直到今天,林秀娟都认为自己三十六岁以前的履历堪称完美:二十二岁一类本科毕业,二十四岁来魔都与李万翔结婚,二十六岁生下儿子李高梓,三十一岁时丈夫生意场上涉猎颇丰:房市、股市,斩获千万,她也因此妻凭夫贵,干脆辞去工作,安心在家当起阔太太。尽管资产几千万在魔都人眼中不算大富大贵,但比起父辈,比起同侪,比起任何林秀娟所熟知的人,自己的家庭都是美满幸福的,丈夫李万翔在她眼中,更是神一般的存在。
作为一个出生在三线城市的女儿,从小见惯了父母因为房子、存款、赡养老人、学费等等而大打出手,林秀娟三十出头就和丈夫名下有一处魔都顶级地段一百七十多平米的复式楼,两部车,一家公司。尤其是他们的家,三层复式,欧式家装,四房三卫。在这个人均住房面积不到十五平米的城市,林秀娟是知足的。每当夜晚,三口之家,楼上楼下,水晶灯中,光转玉壶,其乐融融!
可此时,披头散发的林秀娟整张脸俯卧在进口的澳毛被里:听不到声音,纹丝不动,连那双黑色粗跟皮鞋都牢牢地套在脚上,不曾脱下。主卧的绛红色窗帘低垂婉逥,仿佛女主人这副模样不忍卒睹。
秀娟这才明白,什么叫欲哭无泪。她只觉浑身发抖,心乱如麻,眼角却无一滴眼泪,倒是十几年前在满目青山的大学校园里吟诵的一句词涌上了心头:山中岁月,海上心情。
她抬起头,看着窗外远处的公园,树木已是光秃秃,在夜风里更显得狰狞可怕。林秀娟苦笑,原来“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是这个意思!
冬天天黑得早,在林秀娟眼里,今天更是如墨般黑。令她一沉到底了。
二、尽道有些堪恨,任是无情也动人
李万翔今天的日子也不好过。早上八点,他就坐在办公桌前看起了月报。看了一个小时,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这对于商海浮沉十五载的他来说,简直是头一遭。从昨晚开始,李万翔就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此后一直心惊肉跳,老觉得会有不祥之事发生。
今天凌晨,他还特意早起,到市中心一座香火颇旺的寺庙烧香,虔诚地在佛像前焚香叩首。可事实上,该来的终归会来。
九点不到,随着“哗啦”一声,秘书白晓丽打开门冲了进来,用比平时高十倍的嗓门夹着些惊慌说:“李总,出事了!”
李万翔此时眼睛仍盯着月报,至少过了五秒,才抬起头,刻意放慢了语速:“什么事?”每逢大事有静气,泰山崩于前而不惊是李万翔的人生准则,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告诫自己不可慌乱。
“在水一方楼盘有个看房的客户死了!”白晓丽慌不择言。
“啪!”李万翔把月报重重的砸在办公桌上,桌上的琉璃烟灰缸被文件夹撞击发出尖锐的刺响,刮得白晓丽耳膜“嗡嗡”作痛。她知道自己说错了话,犯了李总的忌讳。
“一大早,什么死不死的,蠢货,话都不会说!”李万翔愤怒的声音变得有些失态。
白晓丽眼泪都快出来了,她不知道,李总今天的火气怎么这么大。“对不起,李——李总,我说错了,是有位客户出事了。”“说具体点。”
伴着白晓丽有些哽咽的声音,李万翔总算明白怎么回事:原来他们高翔公司承接销售的“在水一方”楼盘出了大事。今天早上一位吴姓客户提早到未竣工的A座楼盘看房。期间,陪同的售楼人员小芳接了个电话,一个疏忽,让这位吴先生自己走到五楼的楼道里。恰好楼道漆黑一团,吴先生摸索走到电梯间,可他不知道这个单元的电梯轿厢尚未安装好,所以一脚踏进了空洞,从十几米的高空垂直落下……
李万翔越听眉头就皱的越紧,几乎要拧成麻花。过了一会,他问:“王总呢?”
王总,王子楠是也,在水一方楼盘开发商。
“打他的电话,说是找他们律师,律师又说是因为我们公司售楼人员没有尽到安保职责,所以要我们负全责。目前暂时是由销售部在处理。”
“王八蛋,缩头乌龟!”李万翔咬牙切齿地吐出一句,“遇到麻烦就躲起来!”他闭上眼,头往后靠在老板椅上,白晓丽知趣地带上门出去了。
李万翔的公司为了赢得这片楼盘的营销权,煞费苦心:做楼书,搞创意,请客吃饭,打通关系……王子楠是个笑面虎,口蜜腹剑,当面拥抱,背后捅刀子的事都做得出。口口声声称“万翔就是我的兄弟,兄弟的忙大哥一定要帮!”实际上背后刁难使绊子的事正是他指使的,他想占李万翔公司的创意为己用,把营销权给自己的小舅子。李万翔没法子,只得花了血本请动了地头蛇,楼盘建设老出乱子,王子楠吃了暗亏,总算答应让高翔公司承接该楼盘的销售。
可眼下又出了这么档子事,善后的工作不知到哪一天才能结束,这还得看家属的配合程度。就怕一些媒体人唯恐天下不乱,盯着这件事大做文章,他们写上一版,就够李万翔他们吃上一壶了。更要紧的是,李万翔也参与了这座楼盘的开发。这十几年来,他的财富程度一直在几千万徘徊。稍有急用,便觉得资金不够用。四十多岁的男人总想赌一把,“此时不搏,更待何时!”加上当初王子楠极力撺掇,“你想想,一个亿进去,十个亿也出来了。到时候你就是亿万富翁了,还用得着这么辛苦?大哥这是带着小弟你发财!”
于是乎,李万翔一时头脑发热,从银行贷款加上自己原有的一部分资金积累凑了一亿入股。当然他这一股在几十亿的总金额里,不值一哂,可这对于李万翔来说,却是自己的全部家当,可以说连身家性命都搭上了。最近银根紧缩,他自己的公司急需流动资金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就等“在水一方”楼盘大卖,好尽早收回股金和红利。这事一出,加之当前楼市低迷,楼盘销售无疑是雪上加霜。
李万翔想到这,靠在椅背上一动不动,简直像熟睡一般。十点多了,冬日的阳光从百叶窗里洒进来,经过桌上那枚水晶球的折射,突然间有一种眩晕的感觉。金底青花的珐琅座钟原本清脆的敲击声,此时却有一种揪心的急促感。
李万翔真希望这都是一场梦,等梦醒了,一切都烟消云散。可他知道,这不过是奢望而已。果然他的手机就在此时响起来,李万翔的梦醒了。
拿起手机,李万翔看到一个熟悉的来电。他按下扬声器,一个声音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好像它的主人被关在里面很久了:
“三弟,在干啥呢?”李万翔排行第三,老家有两个姐姐,打电话来的是二姐。“二姐,没干什么。你找我有事吗?”
“哎呦,怎么一见二姐的电话,就问我有没有事找你。你就不能关心关心妈,关心一下我和大姐吗?”
“嗯嗯,你们还好吧?”
“哦嗬,我提醒你,你才问我,还问得这么勉强。妹,我跟你说啊……”李万翔二姐是村里的计生干部,习惯了这么教训别人。四年前,被自己说了一辈子的男人终于忍不住了,提出与她离婚。二姐这张嘴只好转移目标,放在别人身上,平时李万翔也是能躲则躲,今天也是倒霉,怎么就躲不过了?
他忍不住把手机拿开点,好让这声音离自己远点。想想不妥,又伸手把手机拿过来,按灭了扬声器,以免偌大的办公室里回荡的都是这个扁平粗哑的声音。
听了一阵子,李万翔发现二姐没有结束的意思,只好打断她正在进行的演讲:“二姐,我正在开会,要没其他事,我先挂了。”
“哎哎,你别挂呀,我还有事呢!我家月丹你是知道的,学习学不进,考大学是没指望了,就想着上班赚钱。前段时间跟班里同学吵架了,别人说她成绩不好,将来只有回家种地。月丹性子又好强,就放话出去了,说是‘我舅舅是大老板,有本事帮我找工作。你们就是读了大学,也没我的工作好’……”
“姐,你到底想说什么?”
“这不,这丫头昨天一赌气,买了张去你那的车票,今天中午该到了,说是要去你那找工作……”
李万翔的脑子都要大了,他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有这么“二”的姐呢?他二姐不知,还在继续:“你派个车去接下她吧!十几岁的女孩,人生地不熟的,你做舅舅的,得多操心啊!”
“几点到?车次?哪个车站?”
“哦,你等等,我要找找看。”
至少等了三分钟,李万翔才弄明白他的外甥女到达时间、车次、车站,最后在他二姐意犹未尽的话音中好不容易挂断了电话。
珐琅钟又一次敲响了时间:上午十一点。李万翔按下一个座机键:徐师傅,请侬进来下。在魔都呆了近二十年,他也算是半个本地人,方言也能说上几句。
一个四十多岁其貌不扬的男子走了进来,他是李万翔的司机。李万翔说:
“徐师傅,麻烦侬去趟江南火车站接个人。这是伊的姓名,车次,到达时间。”
“好哇!”
“麻烦侬。”
“咯么李总,我接到后,送伊到啥地方呢?”
“侬先送伊到我办公室里厢。好阀?”“好嗒嗒(好的)。”
安排了曹月丹的接车事宜,李万翔决定自己开车去“在水一方”的事发现场看看,毕竟这才是头等大事。
钻进新买的X6,抚摸着裸色的真皮座套,李万翔才感觉一丝欣慰:有时候他觉得车比人更体贴,更值得怜爱。因为她不会喋喋不休,不会见异思迁,不会欲壑不满。你不需要她,她便安静的呆在那里,如水般的线条优雅却又迷人;需要她时,她便动若脱兔,毫无怨言地载你去任何想去之地。
李万翔打开CD,Sarah Brightman如金石般的嗓音顿时流淌在车厢每一寸空间里。此情此景,令他想起初识周娜的情景,人生若只如初见,只是如今,故人已在春山外。
三、人生若只如初见
同一天,清晨第一缕阳光透过白色绣花的欧根纱窗帘,照进卧室时,周娜已经起床好久了。李万翔三点半起床离开时,她就清醒了。她不问他起这么早干什么去,李万翔也装作不知道周娜醒过来,两个人就在这黑暗中,默默地各怀心事,生怕哪一方忍不住,一开口,便打破了夜漆漆的静。
周娜不吃不喝地站在窗前,马尾辫已经放下,漫卷的长发尾梢偷偷透出些许栗红,白皙的脸庞像煮熟的剥壳鸡蛋。透明的指甲配上纤素的玉手,身上还着一套意大利进口的白色真丝提花睡袍,当真是“翩若惊鸿,婉若游龙。”
事实上,李万翔对周娜的第一印象,却远没有“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颻兮若流风之回雪”的惊艳。
那是多久以前呢!时间并不久远,可周娜觉得恍若隔世。
时光回溯到两年前的冬天。那天正值浦南大学舞蹈系大二学生周娜十九岁的生日,用芳华正茂、光彩照人、青春无敌等等都无法言尽这个年华的美妙。可周娜本人却一点都没感到美好,因为这天她的老朋友来了。
本来女生来例假这也是常事,可周娜有个痛经的老毛病,刚好男朋友方柏阳又不在身边,没人帮她捂暖痛得抽搐的肚子。
现在,她不仅不能抱着热水袋躺在床上,还不得不穿着单薄的大红织缎旗袍,踩着十吋的高跟鞋,盯着冬日的寒风,哆哆嗦嗦地站在“蓝色家园”楼盘售楼处门前。那天正值“蓝色家园”开盘剪彩仪式,周娜和几个同学被请去担任礼仪小姐。
周娜原本可以推脱不去的,可一百五十元一天的收入与她还是诱人的,差不多是她十天的生活费呢!也许省下来可以为自己添件冬衣,她觊觎一件皮草马甲很久了,但正品要一千多元。像她这样的穷学生只能买件仿品穿穿,即使一件赝品也要一百多元,所以周娜默默地对自己说,“为了美,我必须学会忍受痛苦。”
周娜想象得出自己当时的狼狈样:劣质的羊毛袜贴在身上毛绒绒,又刺又痒。活像小虫子在噬咬她的大腿。在冬日干燥的环境中,稍有摩擦就产生静电,旗袍的下摆常常吸附在羊毛袜上,周娜只好偷偷用手将裙摆撩开,一会再放开,反复如此。
剪彩仪式将于十一点开始,周娜和同伴从九点开始站起,十吋高跟鞋踩在水泥地上,久了小腿都要抽筋。她就先把重心移到左脚,支撑不住再换到右脚。
这是站在一旁的安迪笑眯眯的凑近她,低声说:“知道吗?听说中午还有顿免费的午餐呢!”
“嗯,”周娜想,“我早就知道了。”早起时,周娜肚疼得没什么胃口,又听说中午还有顿大餐等着她,干脆连早餐也省下来。如今,不争气的肚子已经“咕咕”直叫,又冷又饿还痛经,浑身瑟瑟发抖,还得绷起笑脸鞠躬欢迎。周娜赌气地想:等拿到这一百五十块,我一定要把那件马甲买下来。
十一点了,上面通知她们:剪彩仪式延时到十二点,说是要等区里一位领导开完会赶过来才能开始。这凭空多出的一个小时简直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周娜的心理期望值是站两个小时,然后坐在暖和的大厅里享受一顿美餐,拿钱走人,捱到十一点就是她的心理承受极限,一旦超过这个极限,多一分钟也是煎熬。
周娜觉得眼前一阵阵发黑,直冒金星,心跳加速,胸前一股呕意涌上,忍不住“哇”地一声吐在台阶上,团云簇锦的旗袍也不幸溅上呕吐物。旁边几位姑娘吓得“哎呀”大叫,因为八个人中最高最靓的周娜居然晕倒在地,脸色苍白,不省人事。
李万翔就坐在周娜身后的大厅里,隔着玻璃门,他能看到八个高挑的姑娘踩着高跷般,大冷天穿着单薄如纸的旗袍立在外面。那时的他,根本不会想到这其中会有一个女孩走进他的生活,走进他的内心,进而影响他后半生的命运。只是低下头看了一条手机短信,啜了一口普洱的时间,李万翔再抬起头看向门外,发现那儿已经围了一圈人,乱成一团。
他并不是喜欢凑热闹的人,但那是他的职责所在——礼仪公司是高翔公司联系,请了这些礼仪小姐前来。出于礼貌,也担心出乱子,李万翔还是迅速站起来。
见李总过来,围观的人连忙让开一条路。高翔公司企划部的杨经理正在大声训斥礼仪公司的领队:“你们搞啥名堂?礼仪小姐晕倒在我们剪彩现场,成心触阿拉霉头是啵?”
朱领队忙不迭地点头哈腰:“对不住,对不住了,我也不知道她身体这么差。她跟我们合作了半年,以前一直很好!……”
“以前一直很好,哪能今天就晕倒呢?正正好倒在大门口,晦气!喔,对了,你们给她们买保险没?”
“啊?这个,这个,”朱领队吱吱唔唔,不置可否。
杨经理正要伸长脖子骂一通,冷不丁听到一个低沉的声音:
“好了!还有完没完,救人要紧!人都晕倒了,还有心思吵,一会孙书记和开发商都来了,你们还嫌不乱?”
一听李万翔的话,大家都不吱声了,赶紧回头去看脸色已经发青的周娜,朱领队也赶紧拔出手机,拨打120。
李万翔这才看清这个晕倒在地的女孩的模样:乌黑的长发用最便宜的黑色皮筋绾起来,束在脑后。十几岁的年龄原应圆润的脸庞,瘦的怕人,看得出这孩子营养不良。即使紧闭着双眼,鼻翼微微翕动,也能注意到那长长的睫毛像一把小扇子,扑闪着又像小夜蛾柔软的翅,别有一种让人怜爱的韵味。再看她的身上,大冬天唯一保暖的就是那条羊毛袜,脚上还穿着丝袜,瘦骨伶仃的脚踝,由不得想搂她入怀,替她取暖。
朱领队从远处跑过来,气喘吁吁地对杨经理说:“怎么办?刚接到120司机的电话,车子堵在路上了,开过来还不知道要什么时候呢。”
杨经理傻眼了:“啊?剪彩马上就要开始了!”
李万翔正蹲下来查看周娜的病情,看她脸色苍白,脉速加快,浑身冷汗,初步判断她是低血糖。听到朱领队和杨经理的对话,一把把周娜拦腰抱起来:“我送她去医院。”那天徐林生正好出去办另外的事情,不在场。
“李总?”
“李总,您不是要参加剪彩吗?”
“我参不参加剪彩无所谓,再耽误下去,这姑娘命都没了!”看到杨经理还要再开口,李万翔拦住他“少罗嗦,赶紧把车门打开!”正在李万翔关上车门即将离去时,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响起:“李总,让我也去吧,我是她的同学,一同去能照顾她。”——是安迪,不知什么时候她已经脱去旗袍,换上原来的服装。只0.1秒的思索,李万翔就颔首同意。此时距剪彩仪式只有半个小时,他只想赶紧把这人带走,现场还有一个乱摊子等着收拾呢!
就在李万翔出现的那一瞬,安迪就注意到他,尽管相貌衣着平平,但这个男人眉宇间透出的自信和霸气绝非常人所有,还有他处理这种突发事件的魄力和果敢,安迪心下飞快地盘算了一把,趁乱把衣服换好,就等着与李万翔同处一车的机会。安迪相信,凭自己的容颜和谈吐,肯定能让这位老总对自己刮目相看。
李万翔拉开后座车门,和旁人一道协力把周娜搬到后座上放好,随手给她搭上一条薄薄的毛毯,就转到驾驶座。一打开车门,李万翔发现安迪已经如沐春风仪态万千地端坐在副驾驶座上,忍不住有些腻歪,一时间也不好请她下车,只有默默地拿车钥匙、松手闸、启动。
“李总,今天真是太感谢您了!”见李万翔一直默默开车,不发一言,安迪觉得有必要创造话题,好让这个男人记住自己。
“你从未见过我,怎么会知道我姓李?”
“哦,我看别人都这么称呼您。我一下就记住了。我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见过一次面的人都能记住他的名字。”
李万翔继续沉默,安迪等了好久,也不见他回应,又搭讪着,笑说:“唉,我这个同学啊,真是一根筋,自己都来例假了,本来可以跟领队说一声就不用来,可人家还是舍不得这一百五十块钱,硬是要挤进来。你来吧也就来了,结果听说中午有聚餐,她连早饭都没吃,省下肚皮准备大吃一顿,结果倒好,便宜没捞着,自己丢脸不说,还给你们添麻烦。真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不过也难怪,谁让人家是从外地小县城来的呢!”
说罢,她边摇头叹气,边用眼角余光斜睃了一下李万翔的侧面,却见他仍像一尊塑像般眼皮都不眨一下,不免有唱独角戏的感觉。不过安迪不是那么容易冷场的人,她就不相信李万翔是个铁人,于是又莞尔一笑:“李总,能给张名片吗?也好让我的同学向您表示感谢!”
“不好意思,今天没带。”其实李万翔的心里已经开始骂娘了:“他妈的,老子还是外地农村过来的呢!”
安迪却不知,只一下被噎住了,倒是沉默了五分钟,待她再要开口,“嘎”地一声车子停在郊江镇上最近的公立医院急诊中心门口。李万翔以他惯有的高效完成了一系列动作:交了两千元押金;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拜托一位医生朋友负责周娜的化验、检查、输液等等。他大踏步走向停车场取车,还得赶回去参加一点的论坛会呢!
李万翔想,自己与这个女孩不会再有交集了。前三十八年时光里,他一直以为人生就像开关车门,打开车门,事情开始;关上车门,事情结束。但他不知,其实人生是砸核桃,不砸开核桃坚硬的外壳,你永远不知道等待你的将是何种果实:是饱满可口,晶莹欲滴;还是干瘪苦涩,腐烂生蠹。这才是人生,信不信由你。
四、世事如棋,从来兴废由天命?
驱车前往“在水一方”售楼处的路上,李万翔也想起许多前尘往事:送周娜去医院的途中,安迪说的那些话,他全都听到了,说得他心潮翻涌,五味杂陈,感概万千。其实李万翔也是这么个出身,来自苦寒家庭,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母亲一个人拉扯大他和两个姐姐。读大学时,比这更狼狈的事情他都遭遇过:帮培训机构半夜张贴广告宣传单,被巡逻人员发现抓起来,以为他大半夜攀墙意图不轨;帮水产批发市场的摊主蹬黄鱼车送海鲜,冬天夜里结冰,路面打滑,黄鱼车整个倾覆过来,二十岁的他摔在冰上半晌不能动弹……
那天李万翔其实很想回头看看周娜,看看那张尖尖的,巴掌大的小脸,微微抖动的睫毛,他甚至能想像出那下面藏有怎样的一双波光流转的眼。但碍于安迪,他只好摒紧双唇,不置一喙。李万翔对周娜既不是同情,也不是爱慕,而是一种说不出的倾诉纠结融合在一起:有惊讶,有痛心,还有些许——悯恤。他原以为只有二十年才有这样的故事,没想到二十年后照样有,而且就在身边,一个女孩要有多么难,才会在来例假的日子,为了区区一百五十块,顶着寒彻入骨的北风,不吃不喝地站在那儿,即使晕倒也没听到她吭一声。
男女之间最忌讳有了情感杂糅缠绕,一旦有了,就像一粒种子滚落心田,俟以时日,它必定以摧枯拉朽之势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那时便是把心放在火上煎熬般。即便“摧烧之,当风扬其灰”,可那灰还在,只要你呼吸,照样会进入你的身体。
一点钟,李万翔已经到了“在水一方”售楼处门前,这是市中心闹中取静的绝佳去处。门前是一条有着百年历史的马路,两旁是浓荫密布的法国梧桐,巴掌大的梧桐叶常常自肩头飘落,十里洋场时这条路曾风光无限。再走过一个红绿灯便是号称魔都最时尚最易轧闹猛的去处——东方大道,多少红男绿女,西装革履,摩登太太从这里走过,谁不梦想着在这里拥有一套房子?在这样的地段有了一套房子,马上跃级千万富豪阶层,出入皆富户,往来无白丁。嘻嘻,可凡人都知道那不过痴人说梦,老百姓还是老老实实地住自己的石库房,公寓楼吧!
“在水一方”左侧是一座天主教堂,赭黄色外墙,哥特式尖顶,淡绿色青铜半弧形钟楼,乍看活像旧时遗老的瓜皮帽,近看又像浸泡在玻璃瓶的大蒜头。整个搭配滑稽又很协调,谁让这是个海上之滩呢!任你好的,坏的,生的,熟的,软的,硬的都放在那锅里炖着,“呼呼”地乱煮一气,倒也有别样的美味。教堂里传出幽幽的琴声,大约是唱诗班在排练,毕竟新年快到了。沉浸在悠扬的天籁般琴声中,李万翔走进了“在水一方”售楼处,立刻被一股扑面而来的人声鼎沸所湮没。
尽管是冬日,李万翔还是忍不住出了一身冷汗。一群人聚集在售楼处的沙盘旁,围成一个圈,嚎啕大哭,其中几位妇女哭到情深处,忍不住眼泪鼻涕乱抹,衣服上、地上、沙盘旁。一位五,六十岁的妇人瘫坐正中,哭天抢地,恨不得以头撞地,油绿色中式对襟棉袄纽扣被拉掉了两只,敞开的胸并不诱人,倒是露出手工编打的平针毛衣,颜色褪得已看不出本色,齐齐套在臃肿的腰身上,像是一只移动的木桶,口里还哭喊:“死鬼哟,你怎么这么早就走了,扔下我和儿子怎么活呀?”——正是死者吴德仁的妻子,旁边搀扶她的中年男子应该是她的儿子吴晓仁。只见他闭目抽泣,却不见半点眼泪,时不时借抹眼泪之机抬眼斜瞄四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