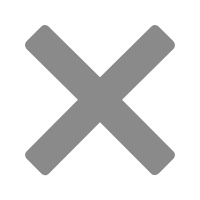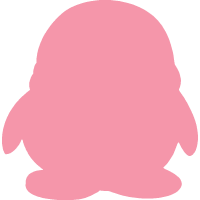第 12 章节
小儿子,好好读书,才能走出这穷酸小村去。要是真读不下去,将来不妨跟着我开三轮得了。”我没有说话,只是痴痴地看着他,他不禁“呵呵”一笑,说声“走了”,就调转车头了。我也只是莞尔一笑,默默彳亍在风雨中,看着他的车影远去,还有那响彻云霄的车音也渐渐远去……
我不是一个画家,但撷取美好的片刻,是我的心愿;我不是一个作家,但记录瞬间的感动,是我的习惯。往后,我几乎每次放学都坐严三轮的车,渐渐的我们也十分熟了,什么都谈,天南地北,大到国家时势,小到家庭琐事。
家乡的石子路凹凸不平,像是铺在河面上,坐在车上一路颠簸,车子就像纸船在水面上摇摇晃晃。我头晕目眩的,脑中仿佛形成了一阵龙卷风,正以惊人的速度旋转着,很快就塞满了我整个脑袋。炎热的夏天,地面像是东北人烘过的炕板一样。严三轮买来两支冰棍,同我一起坐在树荫下乘凉。
“小儿子,今年一上头,我就不会再跑三轮了咧。”他突然冲我说道。
“为什么不跑了?”我满脸疑惑,像个小孩子一样,渴求得到大人的回答。
“哎。现在搞小工的,从原来的每天八十到一百现在都涨到一百二了。农民的谷价在涨,工人的工资在涨,就俺们这跑三轮的还是薄薄两三张。最可恨的是那个油价跟放在咯吱窝里的温度计一样只升不降。”他说的有些激动,脸颊不知是被太阳烤红的还是因为过激,红得跟树上熟透了的毛桃一般。
“那你为什么不把价格适当涨一点?”
“你不知道啊。现在的人只知道自己的难处,谁会将心比心地来体会你的难处。你说我这跑一趟的路费涨点吧,别人说你黑心,活宰人;你说不涨吧,自己又吃亏。整天坐在车上等,时间也耽误了,还患了个坐骨神经,真是不想干了。”
“那你以后干什么呢?”
“回家老老实实种田呗,我打算把以前租出去的田都收回来。只是可惜了我这张老三轮,它是陪伴我时间最长的一辆,风风雨雨,整整十二年了。我这一辈子,就认定两个伴侣,除了我老婆,就是这座下的三轮了。不过你放心,我是不会让它荒着的,有顾客需要的话,我还是会跑。你也可以打我电话,我来接你然后送你回去,价格我不跟你涨,不管别人跑多少。”
我高兴地笑了,取出纸笔记下号码,小心地藏进了包包里。
我记得那个炎热的下午,我们聊了许久。其实,人之相惜惜于品;人之相敬敬于德;人之相交交于情;人之相信信于诚。那么,我和严三轮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后来,我到城里求学去了,回家的次数更少了,当然坐三轮的次数也更少了。渐渐的,我好像真没有再在乡镇上看见严三轮的影子了,看见他傲岸地坐在车上,叼着烟,露出和蔼的笑容。我也便很少租车了,通常回一次家,都是让父亲骑摩托车来接的。每个人的世界都不断地有旧人走出新人走进。再后来,我的记忆库不知何时自觉地便将关于严三轮这人的事给筛选掉了。
又是一年夏至日,一次期末后,我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无意间从包包中抖出了一张邹巴巴的纸条,我轻轻展开一看,上面记的居然就是严三轮的电话号码,我脑中的记忆马上又如重新燃起的篝火。已经有三年多没见到这个人了吧,今日回去一定要再一次坐他的破三轮。
我怀着激动心情从城里搭车到了镇上。镇上的街道口依然停满了摩的与三轮,像是待售的骏马,耐心地等待着拥有伯乐之慧眼的乘客。我到处索寻着那张熟悉的脸,未果,我坐到树荫下,嘴里含起了根冰棍,这才想起严三轮是早已没干这行的了。于是我拨通了他的号码,响了半天才有人接,未等我说话,那边就传来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声音仿佛有些嘶哑、有些沧桑:
“喂!哪位?”
“额,我想……我找一下严师傅。”我一时吞吞吐吐、不知所措了。
对面没有回应了,然后马上就听到一阵“嘟嘟”的挂机声。我感到一阵莫名其妙,以为是自己拨错了,又看一遍号码发现没错又重新拨号,这回响了半天居然没人接了。我在无奈之下感到一种如失珍宝的失落。我走到又一个开三轮的师傅面前,他正在打盹,嘴巴一张一合的,发出“噗噗”的声音,我叫醒了他,他使劲地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小伙子,上哪?”
“不忙,不忙”,我边应和着边从怀里掏包烟来,“师傅,抽根烟,我向你打听个事。”
“什么事?你说”,他很客气接过烟,“这镇上的,我跑得多,路子熟,没什么不知道的。”
“你知道你们同行间有个外号叫‘严三轮’的么?”
“他啊,这个家伙,他我知道!”
“他是不是没跑三轮了?”
“哎息,人都死球了,还跑什么三轮。”
我一听,脸上的笑容顿时如抽了筋一般僵化了,如耳边打响了一个晴天焦雷,震得我心里一阵酸痛。
“什么时候的事?”
“今年开春时。他本来都有两年没跑了,可是接了个老顾客的电话,又兴冲冲地接人去。本来就有坐骨神经,不在家好好养着,偏偏要出去跑,冰雪刚化,路又滑,不想翻车了,当场就死了。”
我没有答话,只是脑海中一幕幕浮现着严三轮披着大绿军衣在风雨里辛苦奔波的样子,还有他那在树荫下吃着冰棍憨笑着的神情……直到我指间的烟头烫到了手指我才醒过来。
“唉,严三轮这人就是太过慈爽了,跑了一辈子三轮不仅没弄到钱享受,还弄了个病、害自己丧了命。这人都是从自己的哭声中开始而从别人的眼泪中结束的,可别人的中间是享受,而他却是痛苦的忍受,真是划不来……”
岁月是这样侵蚀着严三轮的生命,但我不希望严三轮的笑脸会随着时光的年轮在我的记忆中被羽化,于是我再次坐上三轮车,享受着身体的麻木……
怀念我的祖母
我没有见过我的祖父,我是在我祖母的溺爱中长大的。
打我刚记事的时候,祖母就已经六十岁了,我长到上十岁的时候,祖母就快要七十了。
在我家屋后,是有一片园子的。种满了红薯,还有夜来香。
每到夏天的傍晚,夜来香就绽开自己的小身姿,吐出丝丝的幽香,沁人心脾,又在每一个清晨时收拢,就像是定过时的闹钟;每到秋冬,我就会在园子里扒红薯,然后与小伙伴们一起拾柴火来烧着吃,尽管会吃的满脸满手黑炭,但依然吃的很开心。
当然,在这园子里祖母还种下了梨树、杏树、桃树、橘树;黄花、兰花、牵牛花,每到花开的季节,白的白,红的红,黄的黄,蝴蝶、蜜蜂也都凑过来了,十分的热闹。
这片园子,以前其实是一片竹林,被父亲开出来的。记得我小的时候,嘴馋,往往还不等到杏子成熟就偷摘着吃,酸溜溜的;小的时候也贪玩,喜欢爬上梨树,结果把梨树好大一枝给弄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