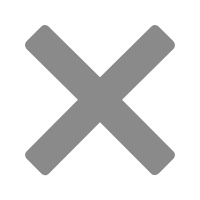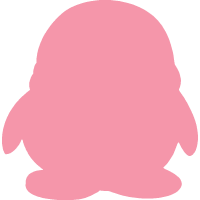第35章老婆婆
我心里更加慌乱了,同时又确定了一点:“这村里的人,果然都有些诡异。”
只听斧头的嗓门一下子抬高了许多,他骂道:“你他妈的,出去问问人,看咱俩谁才渗得慌?我倒是有几个孤魂野鬼朋友,你能好到哪去?一天到晚蹲在你家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谁知道还是不是正经来的呢。”
接着,我就只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夹杂着斧头大嗓门的谩骂,想必是两人“又”打起来了。
是他俩在打,还是他们身边那些我看不见的东西在打?
我不知道,虽然很想知道。
村里的小卖铺,距离棺材铺和刀子的铺子并不远,走出没一百米,就看到前头一个挂着杂货店牌子的商店孤零零的坐落在临街上。
店门口放着一把凳子,凳子上挂着一棵青青的藤蔓,一只黑色的老猫,懒洋洋的窝在凳子上舔着爪子,慵懒而锋利的目光,不时打量着屋檐上飞来飞去的鸟。
听人说,黑猫不祥,我不敢招惹它,远远绕着走了过去,进到了小卖铺里面。
外面的阳光很好,屋子里却并不明亮,勉强可以分辨清楚不多的货物。
我是来买烟的,看到一个木头做的格子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烟,从两块五的白梅到上百的精品,除了看起来个头大了些,跟城市里的烟酒店里没什么区别。
左右看看,屋子里并没有人,于是我伸手去拿一包自己喜欢抽的烟,还没触摸到烟盒,背后传来一声阴测测的走风漏气的声音,沙哑而粗糙:“别动,不要命啦?”
我啊的一声大叫,迅速往旁边跳了开去,并飞快转身。
说话的是一个黑脸的老婆婆,瞎了一只眼睛,穿着不知是黑色还是深蓝色的粗布褂子,同色的棉布的肥大裤子,裤子在脚踝上还收束了一下,扎进黑布鞋中白色的长布袜子里。
老婆婆冲着我笑,我却不敢看她的脸,那是一种吸毒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的病人的脸,憔悴的没有半点生机。
她没多关注我的惊慌和失血的脸色,倒腾着小脚走到那木格子前面,将被我拉起来的盖子重新盖上,又从柜台后面扯出一个巨大的纸箱子,箱子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烟。
“那不是给活人抽的,这个才是。”她从箱子里找出一条我刚才不差点抽出来的那种烟,一边倒着出来一包,一面冲着我笑呵呵地说道。
这时的老婆婆,是冲着门口的,屋外的阳光,终于把光亮投射进了门槛,一点光彩反射在老婆婆的脸上。
那是一张干枯了的橘皮一样皮肤的脸,松弛,苍老,似乎都不可以完全形容透我对这张脸的印象。
就好像是皮肤下面被注入了墨汁,又把脸用钢锉锉过了一样,这样的一张脸,就算在光天化日的大街下看见了,那也吓的人不要不要的,何况这是在并不光明的屋子,屋子又在这个诡异至极的乱葬岗下的村子里。
我紧张的嘴里一阵阵发干,感觉有句话想要说,可是就是说不出来,有动作想做,可就是做不出来。
或许是看出了我的紧张,老婆婆把那包烟拍在我的手里,又吧嗒一下拉了屋里电灯的开关,顿时一片亮堂堂的,渐渐我的心也放回了肚子里。
“看,没啥吧?”老婆婆的脸色在灯光下,终于正常了许多,除了那只坏掉的眼睛还是让我不敢直视,她似乎慈祥地笑道,“就是开着灯,大白天的费电,一月要不少电费来着。”
我看她好像在给我东西,伸手一接,一根带着一点点温度却没有半点人的皮肤该有的感觉,就好像一根蒙了一层血淋淋的还颤颤巍巍挣扎着活动的蛇皮的树枝一样,让我不由激灵灵打了一个长长的寒颤。
低头一看,是一包火柴。
这年头,还有人在用火柴?
“打火机贵,还不顶用,动不动就坏,村里人都不喜欢。”老婆婆弯下腰又把那个放烟的纸箱子放回里面,解释着道,“村里人都不算穷,就是不舍得浪费,火柴就好,一包才三块钱,够一家子用两个月么。这年头,灶下用电,屋里用电,也就上坟啊,抽烟啊,才用得到火柴了,生意不好的很。”
说起日常的生活,这屋里鬼森森的气氛也淡了下去,我浑身的温度又升了上来,但对这老婆婆的话,我又无法接下去。
村里有村里的难过法,城里也有城里的难过法,我自己都活的这么抠抠搜搜,对这老婆婆的日子,我又能说什么呢。
“还要点啥不?”从后面直起腰来,老婆婆笑呵呵地问我。
我这才想起我来找小卖铺的初衷,迟疑着比划道:“那,有没有什么村里的特产,有三十三克,哦,也就是六钱左右的东西,最好是护身符之类的东西……”
没等我乱七八糟的表达完,老婆婆就笑了,道:“你是要镇魂的护身符吧?跟人的魂儿一样重,要小,要精巧,带在贴身的地方,对不对?”
“对对对,就那个。”我连连点头,心里想,看来,村里人对这事情都很在行啊。
老婆婆又弯下腰去,从里面拿出个针线簸箩,里面花花绿绿的一大堆针线活作品,有荷包,有挂饰,也有挂着一枚铜钱的红绳子。
“你挑吧,一块钱一个,看上啥就拿啥,都是一样的。”老婆婆说。
一块钱?这么便宜?
我大吃一惊,看簸箩里的针线工艺品,一个个虽然都是粗布彩绳做的,可精巧无比,放在城里的小饰品店里,那都是能被人哄抢的好东西啊。
这要在店里,那不得三五百块钱才能买一个?
左挑右选,我实在难以决定要什么好。
每一个都很漂亮,我虽然没多少艺术细胞,可好赖还是看得出来。
老婆婆看我为难,还以为我看不上呢,笑笑也没在意:“不行吗?还有从城里进的玻璃玩艺,三块钱一个,也能顶这些用。”
“不不不,不是。”我怕引起老婆婆的不快,连忙摇着手说,“老人家,关键是您的针线活太好了,我真不知道挑个啥才好。”
老婆婆恍然大悟,略有些自得的笑着说:“这年头,可少你这样的年轻娃了,村里人都看不上我这老太婆做的东西。要不,我帮你选个?”
我自然乐得其便。
最后,老婆婆替我选了个红色的中国结一样的荷包,我连忙把一百块钱递过去:“连烟一起,您也别找啦。”
老婆婆很不高兴,我赶紧给她解释:“就您这荷包,放城里工艺品店,没个三五百块钱可买不来,这算我占便宜了都。”
听我说的实诚,老婆婆脸上的阴霾才散去,但她最终还是不肯接受我的好意,我只好把一整条烟都买下,这才算略微心里轻松了一点。
临出门时,老婆婆想起什么似的顺嘴问了我一句:“村里没见过你啊,你谁家亲戚?”
我说我在村长家住的时候,老婆婆一下子不肯再跟我多讲了,等我再说出我是替人来扫墓的之后,她这才对我恢复了刚才的态度,只是叹息:“这造孽的,给先人扫墓上坟,哪能让人代替呢。说句不好听的话,你给人家先人烧的纸,到阴间都归到你先人手里去了。”
我苦笑道:“是啊,可没办法,顾客忙,又想着要尽点心,我没工作,就要找碗饭吃。”
突然,门口门槛上黑影一闪,那黑猫不知什么时候卧在了上头,它死死地盯着我,眼睛里的凶芒毫不掩饰。
我很是吃惊,没招惹它啊!
老婆婆这才仔仔细细把我上下都打量了好几次,犹豫了又犹豫,才把我拉着到了门后,踮着脚趴在我耳边低声道:“后生,看你心善,有句话说出来,你可不要怪我瞎老婆子嘴闲。”
这村里的活神仙多,我哪敢不见山门就拜?!
“您说,您说,我指定心里记着,跟谁也不说。”而且她神神秘秘的样子,显然怕别人知道她跟我说过接下来的一些话,我自然也要给她连声保证。
老婆婆这才安心,低声道:“谁给你说的这个换魂儿的法子,你可要仔细着用,小荷包能替换魂魄,可也能定你的魂魄,有时候啊,这定魂还要比换魂管用,可千万不要自己把自己给害了。”
我一头雾水,老婆婆又道:“你身边有不干净的东西一直跟着,才离开没几天,我这老猫灵醒的很,它可闻到那味儿了,有工夫赶紧找个法子把它赶走,要不然,那可是能要你命的。”
我不禁讶然,这黑猫,这么灵?!
老猫依旧盯着我,一直这样盯着我,就算我离开了小卖铺,直到我走远了,我也仍然能感受到它锐利的目光。
摇摇头,把这头黑猫丢在脑后,我不禁想起老婆婆跟我说的那两句话来。
第二个有不干净的东西在跟着我,这我知道,是高跟鞋。
可第一件事呢?
从老婆婆的口中,我不难听出村长教我的那个“换魂”的法子,其实本应该叫做“镇魂”才对,而换魂只不过是镇魂荷包的附带而已。
他为什么不跟我明说呢?是担心我不会遵照他说的去做,还是别有用心?
我知道,我不应该这么怀疑村长的居心,可昨夜里他家发生的那一切,现在想起来,窗户上那道黑色的影子,那双闪闪发亮的眼睛,都无不在我眼前一幕幕如放电影般的往过演,这不能不让我对村长一家生出提防的心。
他是在帮我,还是在害我?
村长家里神神叨叨的,到底存在着怎样的秘密?
这个村里,有看似精神不正常的疯子,有诡异的村长一家,有妖异的刀子和他的那个我没进去过的铺子,有熊一样雄壮却让我感觉那不是人间的人的斧头,还有这瞎眼的老婆婆,要说这里头没有不为人知的秘密,谁也不会相信。
蓦然间,我突然想起昨晚来村长家的那一对父子,他们到底为了什么事情,居然敢在诡异如村长也不敢走的夜路上找上村长的家门?
我隐隐有一个感觉,如果我能从那对父子身上下手,我在这村里会有巨大的收获,或许,夏小洋的失踪,我也得从他们的身上探查线索。
伸手在藏进贴身衣服口袋的那红色的荷包上摸了摸,我决定问问那父子俩居住的地方,趁着天还没黑,去拜访拜访。
四下一看,又到了小刀和斧头这一对对头的铺子门前。
斧头的棺材早已收回了铺子里,刀子的那对童男童女却还在门口,下午村里有风,风过时,那童男童女哗啦啦的作响,带着它们的黑色的眼珠子都似乎在转动。
我突然觉着,那凉爽黑色的眼睛,分明就是现代化的监控摄像头探头,或许这时的小刀就在半掩着的铺子里坐着,通过这一对诡异的童男童女监视着从他铺子门前经过的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