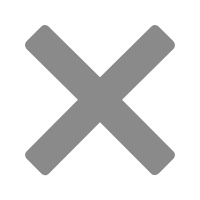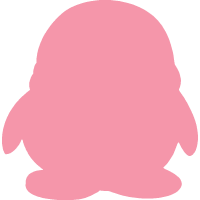第 5 章节
去县城做了趟检查后,回来就对他们说过,我将要去千里之外和我的男朋友举行婚礼,婚后,我就会在那里定居,也许不会再回来了,那我就很难再看到他们的可爱的笑脸了。
我舍不得他们,却勉强自己朝他们笑了一回。那何尝不是含着泪水的笑,何尝不是饱含痛苦的笑。他们没有张口挽留我,个个都沉默着,但我知道他们同样也舍不得我。因为我看到他们将一串串难舍难离的泪水,如断了线的链珠儿一般洒下。我看到这一幕,也早已热泪盈眶,但我还是强忍着,在泪水还没能溢出我的眼眶,我就已经让它们在空气中蒸发了。最后,我笑着说:
“再见了,我的同学们,你们以后要好好学习。”
话音刚落,远处就传来了无情的列车的长鸣。我依依不舍地向列车走去,一步却挪不了三寸,每走一步都会回头好几次。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步伐会这么沉重,离列车还有一段距离,可我却感觉只要一伸手就能够触摸到。我看着他们个个含着泪水,像一棵棵被雨淋湿的禾苗一样,悲凉地立着,我的心口就如同毒虫在撕咬一般地痛。
最后,我还是进了列车,依稀地听到班长说:“咱们为苗兰老师唱一首《好人一生平安吧》吧。”
悲沉的歌声在静谧的夜空中响起,惊醒了无数的栖鸦宿鸟:
“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
有过多少朋友,仿佛还在身边。
也曾心意沉沉,相逢是苦是甜。
如今举杯祝愿,好人一生平安。”
听到这歌声,伴随着无常一般的列车,孩子们像一阵旋风一样追逐着列车不停地跑着、不停地唱着……此时,还能让我怎么忍,还能让我怎么装,我再也按捺不住自己,自由地让这沉痛的歌声过滤我的泪水,我终于失声痛哭起来。
我不知道这群孩子是怎么知道我得了白血病的。是了,班长的家人在县城医院,也许她事先就已经知道了我的病情,但这对我来说在上列车的那刻起就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只知道,我现在正带着这群孩子的真诚的祝福,走完我人生的最后的半年时间……
故乡民歌在我心中
“正月里等我的郎唉,是新年哟
情郎我的哥哥哟,一走大半年
没得哪一天,站在妹面前
站在妹面前,郎呐……”
哦!这是故乡的现代花鼓戏,民歌《十二月等郎》。
每当这婉转悦耳、略显悲怆的曲调飘进我的耳膜时,一种复杂又特殊的情感就注上心头。即使在学习之余、旅途乏倦,或是情绪烦躁、心境郁悒时,也会心生感触,物我皆忘,神游其中。
现代花鼓戏没有悠久的历史,不能与京剧、豫剧、越剧、黄梅戏并肩为我国剧坛的“金花”,没有虔诚的膜拜者遍及海内外。然而,“谁解其中味”?却莫过于它的故乡人。
我骄傲,我荣幸,我的故乡是湖北荆门。湖北本就是戏剧的发源地之一,经过成长已经枝繁叶茂了。
当荆门的青年作家黄发清的中篇小说《乡村留守》问世后,跳到了剧作家盛和煜的手里、走进了导演张曼君的眼中。由此,《十二月等郎》这部聚焦农民现实生活的现代戏曲像新生的娃娃一样,有云一般的缠绵、水一般的甜柔、泥土一般的纯朴、绿叶上滚动的露珠儿一般的清新,走进了乡村、走进了泥土里。
有谁知道,就是这样一曲毫不起眼的《十二月等郎》正唱出了曾经农村妇女的心声。又有谁能体会到这样普通的女人们因男人外出打工而留守乡村,从无奈地被动留守到主动地操持家业;由传统的依附男人到现代的自立自强。最终用柔弱的双肩扛起生活的重担,超越贫穷与寂寞,创造属于自己的一片热土,建立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儿时的记忆早就开始模糊,只是恍惚记得那年镇上的几个大队组了一百多号青年男子到河南的铁路上做工,那时父亲就是其中的一员。当父亲背着行囊和队里的叔伯们坐上队长的拖拉机从我的视线中消失时,我完全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只知道家里剩下祖母、母亲、姐姐和我,父亲很多天都没有回来。
很多次在吃饭的时候,父亲的位置总是空着,我问母亲:“为什么不等爸爸回来再吃呢,他是不是牵着牛去犁地了?我去田里叫他。”母亲拦着我,但一句话也不说,脸上的表情我读不懂。祖母只是坐在门口的石凳上,只有姐姐说:“爸爸去给我们买过年穿的新衣服了,过几天就回来。”
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忙月来了。母亲承担一切地里的活,施肥、打农药、拿着镰刀早出晚归收割稻谷;祖母割猪草,喂鸡;姐姐学会了洗衣做饭,备受邻人的高评;我从此也学会了放牛,村里人叫我“放牛娃”……
突然有一天晚上,我正在门口抓着猫儿和狗儿让它们打架,突然听见一阵久违的哨声。没错!那正是父亲在打口哨,吹着熟悉的《故乡的云》。我高兴地跳了起来,把长满长胡子的父亲迎进家门,激动地叫出祖母、母亲和姐姐,一家人无不欢喜。接下父亲背上沉重的蛇皮袋,里面装满了鲜嫩的桔子,我和姐姐高兴地剥着、吃着,笑着。只有母亲的表情我无法理解,只知道那晚我第一次见母亲流下了泪……
我本以为那段历史会连同我的记忆一起,如同沙滩上的脚印一样,被岁月的潮汐冲去,永远不再出现。然而,直到多年以后,听了《十二月等郎》,我突然想起这一幕,方才明白那时的母亲脸上是挂着荒凉、眼中是溢着叹息……
现在,我又踏上故乡的路,听着故乡的民歌,物我皆忘,一股热流以惊人的速度在体内奔流。这几年,政策开明,家乡业兴人和,丰衣足食。虽然风风雨雨渐渐染白了当年那群女人们的两鬓,但现代花鼓戏仍青春勃发,荆门民歌依然不朽!
独白觊觎
昨夜的雨给今晨的一切都换了一套新装,雨后的湿土的气息,宛如一首赞歌;清晨的静谧有着婴儿熟睡后的可爱,但是天空似乎还阴沉着脸,偶尔有一角似乎泛着羞涩的红晕。
走在路上,有汽笛声沉闷、压抑而又纠结地从远至近驶来,如洪水般遍布整条街道。我为它驻足停留,看着这辆蓝色的轿车缓缓地从我的身前划过。我沉默着,也疑惑着。它莫不是载着满车的觊觎,沉甸甸,沿途洒下未来的希冀?它莫不是载着满车的希冀,沉甸甸,沿途寻找原始的觊觎?未等我的痴想沉淀下来,它早已又从近至远地消失在我的视线中,我的耳膜也不再反弹它的声音,良久……
不知何时,一丝柔和的光线透过残留在树叶的晶莹的水珠倾泻在我慵懒的心上。
隐隐约约中我感到一阵陌生而又似曾相识的傲然的声音在问我:“你是在雨后的阳光下信步还是别有意图地在寻找着什么?”
是的,我是在散步也同时是在找寻。但是那奔驰的轿车犹在寻找内心的觊觎,犹如乡试的秀才在寻找前方的乌纱,那么此时的我虽然说在寻找可又在寻